20.塔爾
「今天可不是釣魚的好日子啊,」我說,「你和我們一塊兒回家吧,我明天一大早就帶你去河邊抓魚。」
「讓我想想……它是在……是在1888年造的,」比利大叔說,「我記得這個,是因為第一個過橋的人是皮博迪,他到我家來為喬迪接生。」
「是的,沒錯。肯定會繼續下。」
「我就知道橋會垮。」阿姆斯迪德說。
「沒事,」我告訴他,「今天早上我還餵過它們呢。你那輛車看上去也沒事,沒有什麼破損。」
安斯在門口迎接我們。他把鬍子颳了,但颳得並不高明,下巴上拉出一道長口。他穿上了禮拜天才穿的褲子,一件白襯衣,領扣也扣上了。襯衣光滑地貼在他的駝背上,看上去背部比平時任何時候都更駝,像是穿白襯衣就會出這種效果。他的面部表情也有一些異樣,現在正眼瞧咱們鄰里,很有些莊重的樣子,面容凝重悲傷,我們走到門廊時他還跟我們握手。我們進門之前颳去鞋底上的泥土,身上穿的禮拜天衣服有些僵硬,窸窸窣窣作響;他一一招呼我們,我們卻沒有正眼瞧他。
「她得到了她的酬報,」我說,「不管她去了哪裡,她終於擺脫了安斯·本德侖,這就是她的酬報。」她在那副棺材盒子里躺了整整三天,等達爾和珠爾先是回到家裡,然後去弄一隻新車輪,再回到他們車子陷在溝里的地方。安斯,就用我家的大車吧,我說。
「人站在濕木板上是容易滑倒的。」奎克說。
「依我看,上帝是會幫忙的,」奎克說,「迄今為止,安斯不都是有上帝在關照嗎?」
歌唱完了,聲音顫抖著越來越輕,停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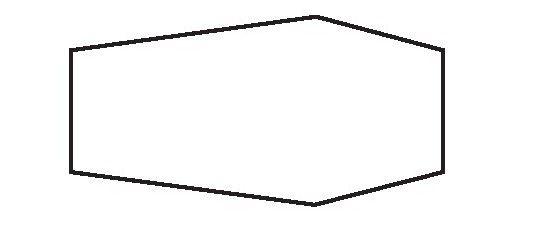
「又多了一個過不了橋的人,再也過不了啦,」阿姆斯迪德說,「他們用車子運送她到城裡得花兩三天https://read.99csw.com時間呢,運到傑弗遜再回來得花整整一個星期。」
人們抬頭望了我一眼,帶著一種詢問的目光。
我們都往外走的時候,維特菲爾德才姍姍到來。他進屋時,腰部以下全濕了,還沾滿了稀泥。「上帝給這家人慰藉,」他說,「我遲到了,因為橋給衝垮了。我繞道去了老淺灘,騎馬蹚水過河的,上帝保佑了我。願上帝的恩典也降臨這戶人家吧。」
「這話一點不假。」利托江說。
小男孩不在那兒。皮博迪告訴我們:小孩如何闖進廚房,發現科拉在烹制那條魚,於是大喊大叫著撲上前去,抓扯科拉;科拉又是如何把他拽到穀倉才了事的。「我那兩匹馬沒事吧?」皮博迪問道。
「馬車要是有什麼地方損壞,我願意幫你修好。」我說。
「看樣子還會下雨的。」
「太倒霉了,」我說,「不過那時你能有什麼辦法呢。」
人們站起身來的時候,安斯到門邊來瞧了瞧我們,於是大家又回門廊去,再一次仔細刮掉鞋底上的泥土,在門口磨蹭一會兒,彼此謙讓著等別人先進去。安斯站在門裡面,莊重而又矜持。他揮手示意往裡走,然後又領著大家進入房間。
「他是鐵了心要送她去傑弗遜。」奎克說。
「比利,要是你老婆每下一次崽我就得過一回橋的話,那橋早就沒了。」皮博迪說。
「這雨來勢挺猛的。」
「那時你能有什麼辦法呢。」我說。
「都是那些娘兒們不好,」卡什說,「我那樣打造是為了她的平衡,我是比照她的尺寸和體重來設計棺材的。」
「那他最好趕快動身。」阿姆斯迪德說。
我們又回到擱凳和短截木板之間,有的坐下,有的蹲著。
「你得說,是上帝一直在護著它的,」比利大叔說,「已經二十五年啦,我沒聽說過有誰動過鎚子去修補過。」
大家都笑了,聲音忽然大了起來,過後馬上又變得安靜,大家都迴避著彼此的目光。
「那時你能有什https://read•99csw.com麼辦法呢。」我說。
要是濕木板會使人滑倒,那麼這鬼天氣結束之前,準會有不少人摔倒的。
屋子裡,女人們開始唱聖歌了。我們聽見第一句歌詞響起,入調之後歌聲變得嘹亮起來。於是,我們趕忙站起身朝門口走去,一面摘下帽子,吐掉嘴裏嚼的煙草。但是我們沒有進門,而是停下來在台階上聚成一群,雙手鬆松地握著帽子,放在身前或背後,一隻腳伸在前面站著,頭低垂下來,目光不是落在手裡握著的帽子上,就是看著地面,或者時不時地看一眼天空,瞟一眼旁人莊重沉靜的面容。
「橋造了有多久了,比利大叔?」奎克問。
這時,維特菲爾德開始講話了,聲音聽起來比他的個子更壯實,好像兩者不屬於同一個人;他是一個,他的聲音是另一個的;兩人並肩騎在兩匹馬上,蹚水過了老淺灘來到屋裡,一個身上濺滿泥漿,另一個連衣服都沒打濕;一個興高采烈,另一個垂頭喪氣。屋子裡有人哭了起來,聽上去彷彿她的雙眼和聲音折返體內,傾聽著。我們挪動了一下身子,把重心移到另一條腿上,彼此目光相接卻又像沒有接觸到似的。
女人們陸續進屋去了,我們能聽見她們談話和扇扇子的聲音。扇子啪嗒、啪嗒、啪嗒作響,談話聲卻有點兒像一群蜜蜂在水桶里嗡嗡作聲。男士們進了門廊就站在那兒,隨意交談幾句,大家誰也不正眼瞧誰。
「我看,上帝跟我們周圍的人一樣,」比利大叔說,「關照到現在,不管也不行啦。」
維特菲爾德終於停了下來。女人們又開始唱歌。氣氛凝重,她們的歌聲像是來自空氣,匯到一起后飄來飄去,帶著哀傷而又令人寬慰的調子。歌唱完了,歌聲彷彿遲遲不散,像僅僅是退進了空氣里;我們要是身子一動,歌聲又會釋放出來,重新瀰漫在我們周圍,哀傷而又令人寬慰。女人把歌唱完了我們才戴上帽子,動作有些僵硬九-九-藏-書,像是我們從來沒有戴過帽子似的。
「我正朝著我主和我的酬報大步前進。」科拉唱道。
「賞賜的是耶和華。」
「沒有誰搞鬼嗎?」他說,「我真想花點錢弄清楚,馬跑掉的時候那小孩在什麼地方。」
「你跟我們走吧。河裡是抓魚最好的地方。」
「賞賜的是耶和華。」我們說。
「去得卻很慢,不會罷休的。」
「這樣的天氣,你是不是有感覺?」阿姆斯迪德問他。
每個結合面和接縫口都做成傾斜面,用刨子刨光,合起來嚴密得像一面鼓,精巧得像個針線盒。人們把她頭腳倒置,是為了不弄皺她的衣服。那可是她的結婚禮服,下擺呈喇叭狀;頭腳倒放,裙子的下擺就可以展開了。人們還剪下一塊蚊帳布給她當面紗,以免顯露臉上被鑽破的地方。
我們補完洞眼之後,我回到屋前。這時男士們已經離開屋子,到了屋前的地方,有的坐在木板的兩頭,有的坐在鋸木擱凳上。這是我們昨晚打造棺材的地方,他們坐的坐,蹲的蹲,都在等候還沒到來的維特菲爾德牧師。
人們頭腳顛倒地把她放進棺材。卡什把棺材做成了個座鐘形狀,像這樣:
回家路上,科拉還唱個不停,她唱道:「我正朝著我主和我的酬報大步前進。」她坐在馬車上,披巾裹著雙肩,沒有下雨卻支起雨傘。
卡什沒有答話。
我轉到屋後去。卡什正在那兒填補小孩在棺材蓋上鑽的洞眼,他一根又一根地削木條,濕木棍子削起來很費事。他本來可以劈開一個罐頭盒子,用鐵皮把洞一一蓋上,誰也看不出有什麼兩樣,至少是誰也不會在意的。我看見他像是在做玻璃活兒似的,一小時才削好一條木楔,其實他滿可以隨地撿起十多根木棍,一一敲進洞眼,那不也行嗎?
「二十八英尺四又二分之一英寸,大概是這個高度吧。」卡什說。這時我挪近他身邊。
「一直關照到現在,欲罷不能了。」阿姆斯迪德說。
「我告訴他了,」奎克說,「他說他估計兩個孩子read•99csw•com已經聽說了,卸了貨現在該是在回家的路上。他說他們能裝上棺材過橋的。」
「那座橋啊,那座橋在那兒很久了。」奎克說。
「安斯幹嗎要急著運送她去傑弗遜,非去不可?」休斯頓問道。
「唉,」比利大叔說,「就像是有這麼一個人,一輩子什麼事兒都無所謂,卻忽然死著心眼要干某件事,這可給他認識的所有人帶來了大麻煩。」
「這是實話,」利托江說,「一點不假。」
「還算卡什運氣,他摔下來只斷了一條腿,」阿姆斯迪德說,「弄不好他會一輩子卧床不起的。卡什,你是從多高摔下來的?」
「是呀,現在要想過河得靠上帝幫她了,」皮博迪說,「安斯是辦不到的。」
這時卡什出現了,他換上了一件乾淨的襯衣。他的頭髮還是濕的,梳得服服帖帖,整齊地搭在腦門上,那又黑又亮的樣子就像他塗了油彩在頭髮上似的。他來到我們中間,僵直地蹲下,大家都瞧著他。
「他是答應過她的,」我說,「是她要這樣做,她是那兒的人,非去那兒不可。」
「都是那些娘兒們不好。」卡什說。
「快弄好了,」我說,「他正要釘上釘子。」
「有許多走過這座橋的人,今後怕是過不了任何橋了。」休斯頓說。
我們在離開安斯的家大約一英里的地方,看見小孩坐在一個爛泥塘的邊上,我從來沒聽說過這塘子里有魚。他轉過頭來看著我們,眼睛睜得大大的,神色鎮定,臉上骯髒,一根釣竿橫在膝頭。科拉仍然在唱歌。
我再次來到安斯的家,已經十點鐘了。皮博迪的兩匹馬拴在馬車後部,它們已經把這輛平板馬車從出事的地方拖回來了。奎克在距小溪一英里遠的山溝發現馬車翻了個底朝天,橫跨在溝上。馬車是在小溪旁給拖出路道的,這兒早已有十多輛馬車出過事。發現馬車的是奎克,他說溪水已經漲了,而且還在上漲。他說溪水已淹過橋樁上他所見過的最高痕迹。「那橋可經不住這樣大的水呀,」我說,「有誰把這告訴安斯了
read•99csw.com嗎?」
「肯定會下。」
「這裏面有一條,」他說,「杜薇·德爾看見過的。」
「你好,弗農,」人們跟我打招呼,「你好,塔爾。」
「他最好還是別想過這橋,就把她埋葬在紐霍普得了,」阿姆斯迪德說,「這座橋老了,我可不願跟它開玩笑。」
我才不管多少人摔倒呢,我關心的是棉花和玉米。 皮博迪也不會在乎人們摔不摔倒。是不是,大夫? 那是事實。地里遲早會被沖刷得乾乾淨淨。似乎總會有事兒發生。 那是當然。所以,東西才會值錢。要是什麼事兒都不發生,人人都獲得大豐收,你以為還有人會費力去種莊稼嗎? 哼,要是我喜歡看見自己種的莊稼在地里被沖得一乾二淨,那我就不是人,那可是我用汗水澆灌出來的呀。 那是實話。除非一個人有本事叫下雨就下雨,他才不會在乎莊稼被沖走。 誰有那種本事?他的眼珠子該是什麼顏色? 對啦,是上帝讓莊稼生長,是他認為該把莊稼沖走才沖走的。
「摔斷過骨頭總是會有感覺的,」利托江說,「斷過骨頭的人能預知天氣。」
「安斯也是非去不可的。」奎克說。
「就在這兒,」他說,「杜薇·德爾看見過的。」
我們要等我們自家的,他說。她會想這樣的,她一向是個特別挑剔的女人。 第三天他們回來了,把她載上大車,這時動身已經太晚了。你們只好繞遠道去過薩姆森家那兒的橋了。你們到達那兒得花一天的工夫,從那兒去傑弗遜還有四十英里。安斯,就用我家的大車吧。 我們要等我們自家的,她會想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