屹立或者毀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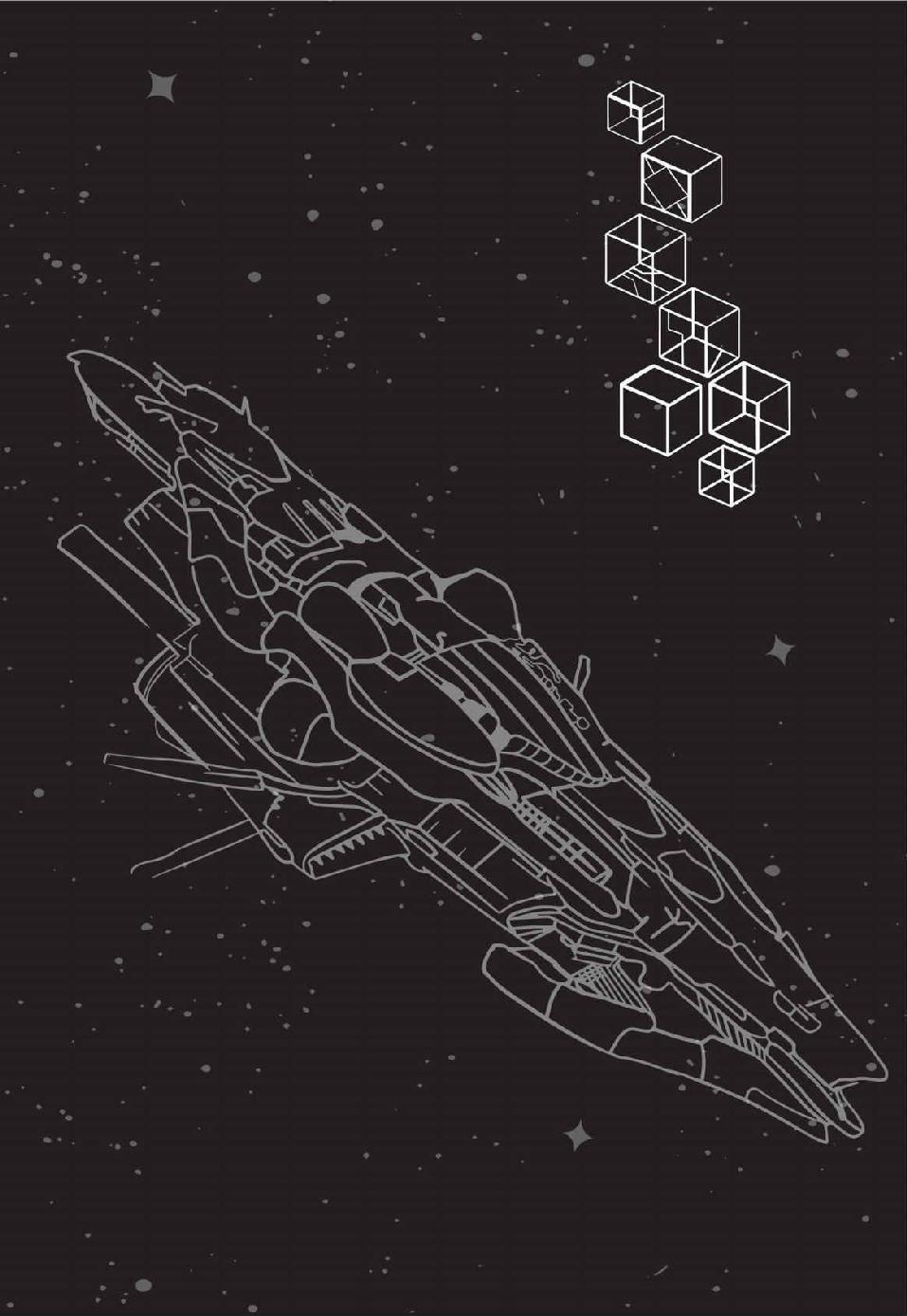
獻給澳大利亞珀斯市Swancon 40的組織者和參加者,這個中篇和這本小說就是在此處完成的。哈哈,我有沒有說過我會這麼做?
一
「看穿攻擊勒雷伊人,其實是我在吹牛?沒,我說得頭頭是道。因為這正是殖民防衛軍會做的那種事情。」
「同意。」亞本維說。
「而你會明白,中尉,我不確定知道這一點對我能有什麼影響。」
「所以你認為你是個雇傭兵。」
「一個多世紀沒發生過這種事了。」我說。
「中尉,我們失去那幾個星球之後,大量人口湧入殘餘的星球,根本找不到工作。你們和奧賓人不只縮減了我們的軍隊,還殺死了我們的經濟。我出生於名叫弗依加的殖民星球,但我們失去了它。我被重新安置在布爾尼,工作機會基本上都給了布爾尼當地人。」
對這兩個勒雷伊人來說,這個人就是我。
「中尉……」特萬拖長尾音說。
「現在的看法是沒必要多等,」我說,「就在咱們交談的時候,行動已經展開。事實上,原本調往喀土穆的一些飛船得到了新的任務,這件事目前在防衛軍內擁有最高優先順序。」
「但關注此處情況的不只是喀土穆人,」亞本維對巴雅說,然後看著我,「你接下來想說的就是這個,對吧?」
「你還想和他交朋友?」亞本維問,「我不認為這個戰術有可能奏效。」
「他沒看穿?」
「要是我拒絕呢?」
「而現在平衡者正在重塑殖民聯盟。」亞本維說。
「殖民聯盟在殖民星球上並非全無朋友,」亞本維說,「還有他們的政府內部。人們向我們輸送情報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那麼,他們的下一步是什麼?」哈特問。
「你不擔心我試圖殺死你,然後逃跑。」特萬說。
「我認為事情和計劃宣布獨立的那些星球有關。」我說。
「你在戰場上肯定殺過很多。」特萬說。
「我和我的內閣主張非暴力不合作是一碼事,」岡田說,「放著三點六億人口毫無防備地面對殖民聯盟是另一碼事。我們與平衡者的協議是防禦和威懾,而不是進攻。」
「我不認為真的失敗了。」我說。
「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想要這種狀態?」哈特說。
「不怎麼擔心,」我說,「你看,我是殖民防衛軍的士兵。你通過親身經歷應該知道,我們經過基因改造,比未經改造的人類更快更強壯。儘管我很尊重你的英勇,指揮官,但假如你試圖殺死我,恐怕要有一番苦戰了。」
亞本維推開椅子起身,臉上露出明顯的厭惡。
「『扯淡』?我知道你多半能猜到。我對你這個人也感興趣。」
「我要保守的秘密比他少得多,」拉烏說,「另外我也不想死。」
「謝謝。你這麼說很貼心,雖然你未必有多少誠意。」
「他發生了什麼?」
「對,我知道,」亞本維說,「殖民聯盟的一名戰俘。」
特萬再次沉默下去。
「當然不在。正如你含蓄地指出的,我只是一名中尉。但這個承諾並非來自我,而是來自殖民防衛軍和殖民聯盟平民政府的最高層。披露所有情況,等這些事結束——不管是什麼事,不管它在什麼時候結束——你會被交還給勒雷伊政府。他們如何對待你就是另一碼事了——前提是他們確實和平衡者組織有瓜葛。即便如此,假如你特別配合,我們甚至會儘可能假裝不知道你是一個最優等的情報源。我們會假裝以為你只是一個普通的軍事指揮官。」
「什麼意思?」
「來自誰?」
「等一等!」岡田抬起一隻手懇求。亞本維停下腳步,「我們和平衡者做了交易,沒錯。但只是為了當且僅當殖民聯盟襲擊喀土穆星本土時保護我們。一艘防衛軍飛船停留在軌道上不會觸發這項交易。」
「比起你知道的事情,我更感興趣的是你聽說的消息。傳聞和推測,諸如此類的東西。我們都是士兵,科特林。儘管我們屬於不同的種族,但我認為我們多半有一點共同之處:我們的工作大多數時候都很無聊,因此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和朋友一起扯淡。我感興趣的是那些東西。」
「所以呢?然後?」
「我是喀土穆星的首相!」岡田的聲音在顫抖。
「說起來,我還真的思考,」我微笑道,「但過度思考是我的壞習慣。我必須承認我是個怪人。」
「要記住,平衡者的發動者之一在我們的國務院身居高位,」我對巴雅說,「我們對各殖民星球獨立運動的了解完全有可能基於受到嚴重篡改的情報。奧坎坡落網之後,平衡者無疑會改變戰術。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
「我們沒有多少時間了。」亞本維對她目前的智囊團說,此刻,他們包括她的助手希拉里·德羅萊特、錢德勒號的船長涅瓦·巴雅、我的朋友哈特·施密特和我。我們全都擠在那個小房間里。「用不了多久,平衡者就會發現他們的偷襲失敗了。」
「我猜他恨你是因為你太忠誠了。」
「一份穩定的工作。」
「意思是摧毀殖民聯盟,對人類存續並不是無關緊要的小事,」我說,「搞不好我們還沒弄出點新名堂來,就已經徹底滅種了。」
「對,行不通。」亞本維贊同道。
「你在平衡者組織內的經歷,」我說,「從最簡單的問題開始:你怎麼會和他們牽涉到一起去?」
「這是個非常現實主義的看法,科特林。」
「你還沒有被拉去做這個手術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我出於對你以前身份的尊重,給你一個選擇,」亞本維繼續道,「說清楚你知道的所有事情,就現在。不得吞吞吐吐,不得刪減撒謊。從你和平衡者的交易開始。老實交代,你還是你,否則就不是了。」
「奧坎坡國務卿非常配合,」我說,「喀土穆宣布獨立時,他告訴我們說響應而去的飛船很可能會一頭撞進陷阱。錢德勒號湊巧在躍遷點附近——殖民聯盟也不想派遣大型艦隊去火上澆油——於是任務就交給了我們。」
我指著她表示強調:「但是,你要明白,這是勝利的條件。」
「怎麼說?」
「那你最好儘快熟悉牆壁。」達昆說。
「為什麼這麼說?」巴雅對我說,「圖賓根號沒有被完全摧毀。偷襲它的兩艘飛船被摧毀了。襲擊我們士兵的勒雷伊人遭到反擊,勒雷伊人全滅,只留了兩個俘虜。喀土穆星沒有獨立。要是說有什麼後果,那就是引來了殖民聯盟更強硬的直接關注。有二十艘防衛軍飛船正在前來的路上,就是為了表明態度。」
「你願意的話自己戴上好了,」我說,「但假如我是你就不會。」我打開門,扔下特萬盯著桌上的頸圈。
我停下腳步,轉身看著我的朋友。「假如他說的都是實話,哈特,那咱們就算是被|操了個天花爛漫。」
「我贊同,非常贊同。我認為你會發現我的上級也會贊同。」
「你能做什麼?」特萬說,「一個小小的中尉。」
「『堅守陣地』這個說法很有意思,」巴雅說,「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武器。殖民聯盟擁有全部的軍械。無論他們受到的是激勵還是激怒,殖民地都不會誤判殖民聯盟的立場,也就是派對已經結束了。」
「為什麼?特萬不是告訴了你平衡者的計劃嗎?」
「凱南是一個成為朋友的敵人,」我說。「儘管我們對他做了很可怕的事情——對,非常可怕——他依然選擇在我們之中尋求友情。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點。」
「不,」特萬說,「假如你對我沒有任何要求,就不會帶著名單來找我了。」
「這個任務,」我說,「還是你從一開始就合作的那組人嗎?」
九九藏書「你認為我們會殺死你嗎,科特林?」我問。
「但背後肯定有個什麼目標,」巴雅對亞本維說,她轉向我,「你看,中尉,我明白你對編織的這套錯綜複雜的行動之網懷著巨大的熱情,我不想說這有什麼不對的。但平衡者這麼做不可能只是為了好玩,他們不是虛無主義者,其中必定有什麼目標,必定有什麼計劃,最終必定要導致什麼。」
「你的小隊忽然變成了一個更大組織的一部分,你沒有任何想法?」
「但我們一直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就讓事態發展到這個地步?」
「好,」巴雅說,「但他們失敗了。喀土穆依然在殖民聯盟內。它沒有摧毀殖民聯盟。」
「你們和種族聯合體害得我們幾百萬人失去工作,流離失所,」特萬說,「當然會見到我們有許多人參與平衡者的行動。」
「而我們對平衡者的插手一無所知。」
「給你個提示,」達昆說,「就是我逃跑時從你們手上劫走的那個人。」
岡田面頰上的斑駁紅斑消失了,他的臉色變得慘白。「你說什麼?」他說。
「作為善意的象徵,」我說,「另外,假如你選擇不和我談,也不需要擔心受到懲罰。」
「曾經,」我說,「但現在做不到了。另外,撇開單一源頭為其自身目標而阻塞所有信息流通的哲學問題不說,這麼做本身也會產生問題。」
「這條路現在不怎麼行得通,大使。」巴雅說。
「因為它對某些人來說非常有利,」我說,「咱們別自欺欺人了,哈特。它對我們來說非常有利。對人類。更確切地說,對殖民聯盟。一個政府體系,穩定運行了數百年,根基是殺得其他人丟盔卸甲,奪取他們的土地。從古到今,每一個成功的人類文明都是這麼做的。難怪我們有些人想重新投向它,哪怕冒著毀滅殖民聯盟本身的危險。因為只要我們回到那條路上,我們肯定比其他所有人都兇惡。」
「這套計劃有個小細節沒能成功,」巴雅說,「種族聯合體堅持了下來。」
「平衡者想要什麼?」我問眾人,「他們想破壞殖民聯盟的穩定並顛覆它。當然還有種族聯合體,但咱們暫時只說我們。」
「我已經被俘,」特萬說,「他們肯定會改變計劃。」
「好的,中尉。」
「我們清楚你不知道高於你所在級別的任何事情,」我說,「我們不指望你知道平衡者的秘密計劃。」
「我不知道,岡田首相。」亞本維說。不知道他有沒有注意到,她對他使用了尊稱,因為此刻他在為他應該代表的那些人著想,而不僅僅是他自己。
「我說過了,他要保守的秘密比我多得多。」
「你忘記我了?」達昆說,「我受到了傷害,指揮官。因為我對你記得非常清楚。我記得你威脅要把我的飛船炸個稀爛。我記得你打死了我的船長和大副。我記得你和奧坎坡國務卿討論如何最有效地屠殺我的全體船員。對,指揮官。我對你的記憶有厚厚的一大堆呢。」
「你們打算什麼時候動手?」
「啊哈,」我說,「你看,現在你全都想起來了。這是錢德勒號,指揮官。這是你們奪取的飛船,也是你們丟失的飛船。嗯,未必是特指你,而是平衡者整體。我們知道你和這事情有關係。我們知道你不是普通的戰地指揮官。不,先生。你是平衡者軍事力量的關鍵人員。你出現在喀土穆,帶領軍隊把我們的人從天上打下來,你不是偶然接下這個任務的。你來這裏必有原因。」
「你審問兩個勒雷伊人和首相就是為了這個?搞清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我點點頭。「我們猜到你會嘗試這麼說,」我說,「誰能怪你呢?沒有理由向你透露必要之外的情況嘛。可惜,指揮官,我們知道一些你以為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也許你們的情報工作做得很差。」
特萬發出勒雷伊人的笑聲:「所以你不害怕我。」
「你知道我肯定在。」翻譯器里響起又一個聲音。這個聲音與翻譯器里我的聲音稍微有點區別,幾乎我話音剛落就響了起來。
「現在咱們去找亞本維,」我說,「然後估計咱們要回鳳凰星空間站,向一大群人彙報情況。再然後,大概是挖個洞躲起來。」
「和你談。」
「平衡者的哲學理念呢?你對它們有什麼看法?」
「嗯,對,」我說,「但在監禁的範疇內,你受到什麼樣的待遇有諸多高低區別。」
「呃,這扇門鎖著,」我說,「基本上給你的逃跑計劃畫上了句號。」
「怎麼死的?」
「對,我認為我得到了想要的所有東西。」我朝兩名士兵點點頭,他們走進房間。我示意哈特跟我走。
「這其中有一些諷刺的感覺。」
「假如我真的殺死了你呢?」
「我們問過了,也還會再問。但這會兒我在問你。你推測一下。」
「不,」亞本維說,「不,你不是。你曾經是,但那是在你參与針對殖民聯盟的公開叛亂之前,是在你命令飛船襲擊殖民防衛軍的艦艇之前,在你下令用陸基武器殺害天空中的防衛軍士兵之前。無論你曾經是什麼人,岡田先生,現在你都是叛國者、殺人犯和戰犯。僅此而已。」
「不是我的命令,」岡田說,「你的士兵炸開我們的地堡,把我拖出來,這時候我才第一次聽說。」
「此話怎講,指揮官?」
「既然你們已經有了奧坎坡,那就不需要我了,」特萬對我說,「奧坎坡的可用情報比我多得多。他是我方計劃的首席架構師。」
「我認為你會驚訝地發現你和我在這方面的分歧有多麼小,特萬指揮官。然而我必須告訴你,你需要說服的人並不是我。討論發生在比咱們高得多得多的層面上。」
「有道理,」我從椅子上起身,走到特萬身邊,它沒有畏縮,「假如你允許,我可以摘掉你的頸圈。」
「假如李中尉的報告完全屬實,那麼她曾向你保證過我們不會殺死你們。」我說。
「就殖民星球的政治而言,殖民聯盟更願意儘可能避人耳目地做事,直到再也無法避人耳目為止。」亞本維聳聳肩,「以前挺成功,已經幾十年了。殖民聯盟抗拒改變。高層有些人覺得事態仍舊可以悄然平息,他們依然能夠控制殖民地。」
「有可能,」我承認道,「但殖民防衛軍的高層不這麼認為。他們目前認為勒雷伊人——你們的政府——積极參与了平衡者組織。你們並不是組織里唯一的種族,這方面我們有足夠的證據。但我們屢次看見勒雷伊人以我們在其他種族身上看不到的方式參与此事。怎麼說呢?有著統計學的顯著性。」
「對,」我說,「這就回到了我想說的問題上,平衡者在最大化它的影響。它不需要花費多少力量就能利用人們對殖民聯盟的不信任,以一個公平交易者的角色出現在各個殖民星球。」我指著亞本維說,「你說我們的時間不多了。我認為正確的說法是我們已經沒有時間了。平衡者肯定正在四處兜售他們編造的事實,等它拿出我們那些飛船懸停在喀土穆上空的畫面,只會向叛亂殖民地證明他們的說法。」
首先,這是一句詛咒。此處的「有意思」無一例外地指「我的天,死亡像雨點似的砸在我們頭上,我們會哀號著慘死,多半還渾身著火」。假如有人想祝福你,他們絕對不會讓你生活在「有意思的」時代。他們會說什麼「祝你永遠快樂」「願你永享安康」https://read•99csw.com或「望你多福多壽」,等等等等。他們肯定不會願你「生活在有意思的時代」。假如有人說願你生活在有意思的時代,大體而言就是希望你死得凄慘,而且死前還要遭受痛苦的折磨。
這個勒雷伊人沒怎麼動彈。
「你可以選擇不和我談。」我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喀土穆會發生什麼?殖民聯盟會如何處理我的星球?我的人民?」
說真的,他們不可能是你的朋友。這個提示我免費送給你。
「是的。」我說。
「沒錯,」岡田說,「你也知道我的身份。」
「但你必須明白,在我工作的這個層級,我們對組織的哲學理念沒什麼興趣。你難道有嗎?你會花很多時間思考殖民聯盟及其所作所為的倫理和哲學嗎?」
「你們還要摧毀我們的基礎設施,導致幾百萬人挨餓。」
「我們搞清楚了很多事情,」我說,「但都不是這個。」
「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份名單的靈感來自於你,」我把另一份列印稿遞給他,「給你,這份你肯定能看懂。」
「我希望你或許能夠表示贊同,中尉。」
「人在河邊走,誰能不濕腳。」哈特說。
「你以為來自誰?」我說。
「你不覺得當雇傭兵有什麼問題。」
「知道上次殖民聯盟派出這麼多防衛軍飛船去一顆沒有直接遭受其他種族襲擊的殖民星球是什麼時候嗎?」
「對。」
「那咱們就開始吧,」拉烏說,「不過這會兒我有個請求。」
特萬朝四周打個手勢:「你摘掉了電擊頸圈。但我依然在這裏,你們的飛船上。我毫不懷疑這扇門的另一側還有一名和你一樣的防衛軍士兵,拿著武器或另一件『刑具』。我不可能逃脫,也無法得到保證,除了眼前這個時刻,我不會因為不和你說話而受到懲罰甚至被殺。」
「但我就是,」特萬說,「我得到的命令內容有限,而且集中在這個任務上。」
「不知道。」我說。
我微笑道:「你說得對,指揮官,這扇門的另一側確實有人。但並不是殖民防衛軍的士兵,只是我的朋友哈特·施密特,他是外交人員,不是殺手或拷問官。他待在門的另一側主要是因為他在操作錄像設備——其實沒有必要,我正在用腦伴錄製這次對話。」
「岡田先生,」亞本維重複道,我看見岡田憤怒得頸部和面部出現了斑駁的紅色,「你似乎有個奇怪的印象,覺得僅憑人格魅力就能改變眼前的局勢,或者用縱橫政壇的響亮嗓門發號施令就能讓我屈服於你的意志。你弄錯了我在這裏扮演的角色,岡田先生。我來見你不是為了阻止你回歸以前的尊貴高位,而是只有我能阻止你變成懸浮在一罐營養液里的一顆離體大腦。」
「自從上次你嘲笑我,我就決定另外找些事情去消磨時間了。」
我指著列印稿說:「因此,殖民防衛軍決定採取行動。平衡者很難找到——他們的組織就是這麼設計的,我明白——因此我們決定不再尋找,而是直奔顯而易見的源頭。這些是我們將在勒雷伊領地打擊的第一批目標,以軍事設施和工業基地為主,但也包括航運和加工中心,目的是讓你們難以裝備和協助平衡者組織。」
「你知道我是誰嗎?」岡田真彥問,聲音里的憤慨分量恰到好處。還是那個房間,但在場人員稍有不同。岡田坐在桌邊。我貼著牆站在門口。他問話的對象不是我,而是坐在他對面的人。
「不僅僅是摧毀,而是破壞穩定,」我說,「防衛軍派遣艦隊不僅是為了接回圖賓根號的倖存者,也是為了懾服一顆反叛的星球。船長,你說他們派了二十艘飛船。」
「這是我們的傳播計劃——我方披露的所有信息都會把事情栽到喀土穆星政府頭上。因此在平衡者看來,你們最後制訂的計劃依然有效。我們希望你能告訴我這個計劃究竟是什麼。」
「沒有理由,」我說,「除了一個小細節,那就是你曾經登上過它。」
拉烏髮出等同於大笑的勒雷伊人聲音:「你自己說的,中尉。我是個雇傭兵。從平衡者僱用我那一刻開始我就是了。平衡者給的薪水不錯,但這會兒他們的報酬我一個子兒都沒法用。另一方面,你隨時可以弄死我。全世界所有的金錢加起來,對我來說都不如我這條命有價值。」
「防衛軍會為此殺死你,岡田先生。行刑手段是將你的大腦從顱骨內剝離出來,安置在與世隔絕的環境內——永無止境、最恐怖的與世隔絕——直到你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告訴他們。等你說完了,他們會送你回到永無止境的隔絕之中。」
「那麼我能告訴你什麼事情呢?」
「你們人類,」特萬過了一會兒說,「說話的那種方式。發號施令的時候也要假裝徵求許可。」
「你說得對,」我說,「具體來說,我打算換個辦法在特萬指揮官身上試試看。」
「我的工作是管理通信,」拉烏說,「我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思考眼前的任務和我身邊的同事上。中尉,我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思想家。」
我微笑道:「你也許會有興趣知道,這正是拉烏技|師給出的加入平衡者的理由。我不想說這是不對的,只想說這無法說服防衛軍相信貴政府沒有資助平衡者。」
「非常簡單,」我說,「你是勒雷伊人。你指揮的平衡者人員也全是勒雷伊人。你在佔領錢德勒號並屠殺其船員時指揮的人員同樣都是勒雷伊人。拉菲襲擊並令其癱瘓的平衡者基地曾經是勒雷伊人的軍事基地,你們種族棄用了它,但沒有帶走那裡的任何系統。相信你也從中看到了一些規律。」
「指揮官,請允許我對你和你對我一樣坦誠相待吧。」
「對。我不是在為岡田的行為辯護。要不是他和他的政府把平衡者請進門,他和這顆星球也不可能落到今天這步田地。但平衡者從交易中得到了它想要的東西。殖民聯盟的監管越嚴厲,人們對殖民聯盟的怨恨就越強烈,不僅在這兒,而是在得知此事的所有地方。」
「不害怕,」我說,「但我也不希望你害怕我。」
「這就引出了我想說的重點,」我說,「殖民聯盟的穩定已經被破壞了。叫來二十艘飛船也沒什麼用。」
喀土穆星地表的報告陸續進來。圖賓根號派遣的一個排士兵——任務是逮捕這顆星球的首相——被陸基防空武器從天空中擊落。救生艇遭到摧毀前跳出去的士兵被同樣的防空武器殺死。
「我不知道你們的時間單位。」
「我們會確保你是完完整整的。」亞本維說。
岡田的視線掃向我。我冷漠地盯著他。我知道我在房間里扮演的是什麼角色:殖民防衛軍會對岡田施行的一切恐怖折磨的沉默化身。儘管現在開口表達我對大腦移除手術的反對似乎不太適合,但我確實覺得這種行為是徹頭徹尾的犯罪。
「我們知道,」我說,「我們有他全部的記錄。問題在於,我們也知道你知道我們有他全部的記錄。拉菲劫走國務卿后,你們必定會這麼認為。也就是說平衡者再也不能使用那些計劃了,你們會制訂新計劃,而且在舊有的時間表基礎上加速執行。奧坎坡能夠進行有根據的推測,但我們現在需要比推測更全面的東西。」
「我就是這個意思,」哈特說,「只是更加簡潔。」
「奧坎坡國務卿,」特萬說,「他當然很配合了,因為你們把他的大腦放進了隔離艙。」
九-九-藏-書「什麼事,中尉?」
有個諺語:「願你生活在有意思的時代。」
「對,」我說,「儘管並不完美。我認為他們更希望摧毀圖賓根號,殺死全部船員,布置得像是喀土穆星政府完全為此負責,將我們所有人蒙在鼓裡。這麼一來,他們就可以把他們編造的版本賣給願意接受這套說法的人。平衡者的戰略之一是讓我們顯得喜歡欺騙和掩蓋真相。它能成功是因為我們事實上就喜歡欺騙和掩蓋真相。」
重點在於:我是哈利·威爾遜中尉。我當亂世人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我覺得我確實更願意做一條太平犬。我朝這個方向也已經努力了很長一段時間。
「我也不會這麼要求,指揮官,」我說。「告訴你這些的重點在於讓你知道,我至少不會將你僅僅視為一個敵人。」
「你的飛船挫敗了對響應喀土穆叛亂而來的防衛軍飛船的襲擊,」特萬說,「你怎麼會知道?怎麼會趕來阻止襲擊?」
「但這隻會嚇住其他的殖民地。」巴雅說。
「我……我不明白你這話什麼意思。」哈特說。
「你聽得很清楚了,岡田先生,」亞本維說,「你宣布你們星球從殖民聯盟獨立,單是這一點就足以讓你被打成叛國者。僅憑這個罪名你就該在殖民聯盟監獄里度過餘生,也有可能他們決定乾脆判你死刑算了。但除此之外,你還襲擊了殖民防衛軍的武裝力量。防衛軍不會輕饒害死他們士兵的人。假如證據確鑿,你,一顆星球的首相,策劃並勾結殖民聯盟的敵人發動了這場襲擊,防衛軍絕對不會放過你。
「我說的是真話!」岡田叫道,「我不希望我的大腦泡在該死的罐子里,明白嗎?我受到了平衡者的誤導。特萬指揮官騙了我。他說他的角色僅限於威懾,他鼓勵我們在其他殖民星球面前宣布獨立,作出表率——也讓他們知道平衡者能像保護我們一樣保護他們。鼓勵所有殖民地擺脫殖民聯盟的統治。」
「對,」我同意道,「和我談。把你知道的與平衡者及其陰謀有關的一切都告訴我。告訴我你們是如何說服十個人類殖民地背叛殖民聯盟的;告訴我你們組織的所謂終局。全都告訴我,從頭到尾,毫無遺漏。」
等達昆離開,我對特萬說:「你不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勒雷伊人。」
我望向亞本維。
「現在會發生什麼?」岡田問。
話雖如此,中國人確實有個說法,這句有偏見的消極攻擊詛咒有可能發源於此:「寧為太平犬,莫做亂世人」。這條諺語既沒有偏見,也不消極攻擊,而且我非常贊同它。
「就像我們在洛諾克擊潰種族聯合體艦隊,」我說,「敵人是四百個外星種族,各有各的武裝力量。飛船對飛船,我們不可能擊敗他們,但我們想摧毀這支艦隊,因此我們把敵人引入我們設下的陷阱,通過狡詐的手段摧毀了聯合艦隊,等待這場慘敗撕裂種族聯合體。」
「這種程度的叛亂是前所未有的,」哈特對我說,他環顧眾人,「哈利和我跟李中尉談過,去抓首相的那個排就是她率領的。她說她最近的所有任務都是去殖民星球阻止叛亂或者鎮壓已經開始的叛亂。這是新情況。」
「所以他是個叛徒。」
「指揮官,」我說,「讓我把話說清楚。殖民防衛軍已經作出決定。他們要襲擊一些目標,而且要狠狠地發泄怒火。它打算襲擊的是剛好擺在眼前的目標。就此刻而言,也就是勒雷伊人的星球。你知道防衛軍的力量大不如前,但勒雷伊人比以前還要弱小,等防衛軍襲擊了你的人民,他們會被炸得幾乎回到石器時代。你的許多同胞將會受苦。想避免這個結果只有一條路——指揮官,唯一的一條路——那就是讓我們去襲擊其他的目標。給我一些目標讓他們去襲擊。指揮官,請幫助我。」
「因此你以為你是個雇傭兵,直到你發覺整個平衡者組織的存在。」
「拉菲,請你暫時退出去一下。」我說。
岡田苦笑道:「顯然因為無論平衡者的計劃是什麼,都和我們的計劃有著本質區別。具體是什麼,我連猜都沒法猜。大使,我只知道我被利用了。我被利用了,我的政府被利用了,我的星球被利用了。此刻我們所有人都要付出代價。」
「那就好,」我說,扭頭望向特萬,「指揮官特萬,允許我向你介紹我們的駕駛員,拉菲·達昆。不,更確切一些,是重新向你介紹,因為你們已經見過面了。」
「我要找加萊諾國務卿。等她知道你和你的殖民防衛軍走狗對我做的事情,你們只是被開除公職都算運氣好了。」
「謝謝你們把武器系統裝回到了飛船上,」達昆說,「用著非常順手。」
「岡田先生。」
「你為什麼不去問他?」
「岡田首相。」
特萬轉動脖子,讓我能碰到頸圈。我通過腦伴發送命令,打開頸圈的鎖,摘下來放在桌上,然後回到座位上。
特萬陷入沉默和——我猜——懷疑。
我點點頭。「我們必須記住的一點是它做這種事是為了實現它自身的目標。」我指著此刻關押喀土穆星首相的超小號房間的方向說,「平衡者給岡田和他的政府開了張空頭支票,然後偷襲了我們。然而受到懲罰的不是平衡者,而是喀土穆。」
「或者激怒他們。」哈特說。
「指揮官,你不覺得這艘飛船有點眼熟嗎?」
其次,這句詛咒總被掛在中國人頭上,然而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就人們能查到的資料而言,它首先出現在英語里,只是宣稱出自中國人之口,原因多半是漫不經心的種族主義加上某個渾球不希望別人記住他說了他們的壞話。就像「哎,不是我說的,是那些中國人說的,我只是轉告他們說的話」。
「這是種族屠殺。」
「所以當我以前的一名指揮官找我加入平衡者的時候,我沒怎麼思考就接受了。他們給我一份工作,給我機會使用我的技能。薪水非常好。另外還能讓我離開布爾尼,我很討厭那地方。」
「你怎麼會出現在這兒?」特萬問我。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不懂那個詞,但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
「你們強加于他的痛苦。」
從我們的角度來說,戰鬥在開始前就結束了。敵艦隻有最少量的裝甲,像煙花似的爆炸了。我們通過標準通信手段和腦伴網路呼叫圖賓根號,評估他們的損失。
「是啊,」我說,「我的重點是我們直到最近才開始知道平衡者的存在。你們的組織在我們的偵測之下隱藏了很久。」
「一名士兵,同樣是他的朋友,應他的要求殺死了他。」
「我認為中尉想說的就是這個,」亞本維說,「他們不需要有下一步,只需要等我們用我們一貫的方法做我們習慣於做的事情。」
「我沒有授權進行那場襲擊。」岡田開口道。
「不,協助他。我們共同參与了幾個項目,他是主導者,我聽他指揮。」
「我明白,但我還沒說完,」我說,「如我所說,你的餘生大概都將是我們的囚犯,待在一個這麼大的房間里。但還有另一個選擇。」
「也就是我們的近五年。很長一段時間了。」
他們活該。這兩艘飛船當時在襲擊圖賓根號,這艘殖民防衛軍艦艇受到召喚,來喀土穆星鎮壓針對殖民聯盟的反叛行為,主使者是這顆星球的首相,他實在應該更聰明一點的。然而他顯然不夠聰明,圖賓根號抵達喀土穆,派遣一個排的士兵去地表捉read.99csw.com拿首相。就在此時,兩艘飛船躍遷抵達,拿圖賓根號當靶子練習射擊。我猜他們自以為能不受干擾地完成任務,但沒料到會有一艘錢德勒號從恆星里殺了出來。
「對。」
我點點頭:「何必要費神去破壞我們的穩定呢?我們自己就會這麼做的。」
「還真沒有,」拉烏說,「雇傭兵團隊和其他團隊沒什麼區別。有時候就是要和其他團體合作,有時候被併入其他團隊。我按時領薪水,和原先那組人一起做事,所以對我來說沒區別。」
「我確實對你有所要求,」我同意道。「我要你告訴我平衡者對喀土穆和其他殖民地的進攻戰略。告訴我,說服我相信,比起這份名單,我們可以將注意力聚焦在更好的目標上。」我再次指著列印稿說,「你沒有理由要相信我,但我還是要向你保證:幫我說服他們,我會儘可能轉移他們的關注焦點。」
「非暴力不合作通常不包括叫來外部力量充當打手。」我說。
「他為什麼想死?」
「不覺得,」特萬說,「有什麼理由嗎?」
「你這麼說恐怕不能鼓勵我坦白交代,中尉。」
「對。」
它坐的椅子非常不適合它的生理構造,但我們沒有更適合的椅子了。椅子放在桌子前,隔著桌子的對面放著另一把椅子。我坐在這把椅子里,伸出手,把翻譯器放在桌上。
「如我所說,我們知道勒雷伊人並不是平衡者唯一的參与者。但我們認為他們是主要參与者。除了掐斷主要輸送管道的價值,我們認為這麼做還可以警告其他所有人:你們可以利用平衡者來摧毀殖民聯盟,但我們依然足夠強大,可以拖著你們一起完蛋。」
「我不明白。」他對我說。
「一份列印稿,列出了殖民防衛軍計劃近期打擊的目標。」我說。
「好,太好了,」巴雅說,「具體是什麼呢?」
特萬接過名單讀了一遍,然後又讀了第二遍,最後把列印稿放在我和他之間的桌面上。
「大約六年。」
「我要告訴他一些他真正害怕的事情。」我說。
但從恆星里殺出來是個很有詩意的漂亮說法。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岡田說,「我們只是宣布從殖民聯盟獨立,沒別的了。」
必須有人去審問這些人。
「但種族聯合體從此徹底改變了,」我說,「洛諾克之前,聯合體是你不可能挑戰的龐然大物。洛諾克之後,出現了一場公然叛亂,第一次有人企圖刺殺他們的首領高將軍。緊張的氣氛再也沒有消退過,高將軍最終死於刺殺。聯合體的現狀是殖民聯盟一手造就的。但換個角度說,殖民聯盟協助創造了能夠讓平衡者下手的客觀條件。」
因此,他們不但不是你的朋友,而且持有偏見,還熱愛消極攻擊。
「假如你們打算攻擊我們的星球,我建議先打布爾尼。」
「我知道特萬對你恨之入骨,因為你願意和我們談。我還知道他企圖攻擊你,讓你閉嘴。」
我最近一段有意思的經歷從錢德勒號——我駐紮的飛船——躍遷進入喀土穆星系,飛快地炸掉了它見到的頭兩條飛船中的一條開始。
「除非我們回不去,而是被徹底抹除。」
「我不明白。」特萬說。
「對,」我說,「平衡者很小,因此必須最大化它的衝擊力。它必須尋求能鬧出響動的異常手段。這是他們從我們身上學到的。」
「是的,應該是的,」我承認道,「不,拉烏技|師。我們沒有殺死你或特萬指揮官的打算。」我望著勒雷伊人的身體鬆弛下來,「事實上,等這些事情完全結束,我們希望能把你們還給勒雷伊政府。」
「比方說平衡者可以編造出喀土穆事件的另一套說法向其他殖民星球宣傳。」亞本維說。
「第一次談話的重點不是和他交朋友,而是讓他不害怕我。」
我們先發射導彈,然後向敵方導彈發射粒子束,在它們撞擊圖賓根號前引爆導彈。我們的導彈插|進敵艦的船殼,目標是破壞動力系統和武器。我們不擔心他們的船員。我們知道不會有船員,只會有一名駕駛員。
「我不知道任何重要情況,」拉烏說,「我是一名技|師。我只知道我這個崗位上別人告訴我的那些事情。」
「我不相信有這個可能性。」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說,「我是說我認識另一個勒雷伊人,和他有個人交情。他是科學家,名叫凱南·蘇恩·蘇。他和你一樣,也被我們俘虜。我被派給了他。」
「什麼?」
「或者激勵他們堅守陣地。」我說。
「我不害怕,」特萬說,「我害怕的是你們種族的其他人。還有假如我不和你談,有可能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死了。」
現實中我們當然做不到這個。我們只是躍遷來到喀土穆上空的位置比那兩艘船和正在遭受攻擊的圖賓根號更靠近這個星系的恆星而已。而實際上,從他們的角度看,我們躲在喀土穆星系的恆星背後,並沒有給錢德勒號帶來任何優勢。敵方的艦載系統也不可能晚一秒發現我們。我們的優勢在於它們沒料到我們會跳出來。我們出現的時候,它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摧毀圖賓根號上,近距離向圖賓根號的弱點發射導彈以擊毀飛船,終結飛船上所有人的生命,害得整個殖民聯盟陷入混亂。
只有兩名士兵從襲擊中逃脫,但她們憑一己之力摧毀了陸基設施,幹掉了與平衡者結盟的勒雷伊人士兵——平衡者,就是這個組織對殖民聯盟和種族聯合體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她們在陸基設施抓住了包括指揮官在內的兩名勒雷伊人。然後她們又完成了最初的任務:逮捕喀土穆星的首相。
「你宣布從殖民聯盟獨立,然後躲藏在一個秘密據點,」亞本維說,「這無疑證明你知道殖民聯盟會對你們的獨立作出響應,會派遣武裝人員來捉拿你。就在我們行動的時候,我們遭到了偷襲。襲擊者不是喀土穆人,岡田先生。而是另一股勢力。」
亞本維也轉向我:「所以,按照你的分析——是不是疑神疑鬼暫且不論——這場遭遇戰對平衡者來說是一場勝利。」
「看守他?」
「你腦袋裡有電腦,」巴雅說,「你告訴我們。」
我笑了:「我們目前沒有這個計劃,但我會記住的。你加入平衡者組織多久了?」
「我們又不蠢,」岡田對我啐道,「我們知道你們會來抓我們。我們藏起來是為了拖延時間,以免你們在尋找我們時摧毀基礎設施和造成平民傷亡。」他轉向亞本維,「我們早就知道我們會被抓住。我們知道你們會派出一艘飛船來抓我們,因為我們很清楚殖民聯盟喜歡用這個手段來暗示只需要一艘飛船就能應付任何內政問題。我們希望被抓住。我們的計劃是非暴力不合作,為其他計劃宣布獨立的殖民星球作出榜樣。」
情況很嚴重。飛船已經報廢,勉強趕在生命支持系統崩潰前疏散了船員。我們在錢德勒號上騰出空間,發射躍遷無人機回鳳凰星空間站,請他們派遣救援飛船和人員。
「威爾遜。」
「但他們還是襲擊了我們。」亞本維重新坐下。
「現在你打算怎麼做?」巴雅問。
「你是殖民防衛軍的一名俘虜。更確切地說,一名戰俘。你在使用武器對抗我們時被俘虜。你直接或通過你的命令殺死了許多我們的士兵。我不會折磨你,也不會殺死你,也不允許你在這艘船上受到折磨和被殺。但你必須明白,你的餘生將和我們一起度過了,」我朝四周打個https://read.99csw•com手勢,「在一個比這兒大不了多少的房間里。」
「殖民聯盟壟斷了信息的流通。」巴雅說。
「因為他本來就快死了,」我說,「我們在他的血液中注入了毒藥,每天給他的解毒劑效用越來越低。他請求我的朋友結束他的痛苦。」
「沒錯,」我說,「但我這個中尉的地位高得不同尋常。」
「我挺喜歡。現在也還是挺喜歡。中尉,殖民聯盟是我們的敵人,種族聯合體禁止我們殖民,包括我們想奪回的星球。你們兩者讓我們過得非常艱難。我不介意以牙還牙。」
「你是岡田真彥。」奧黛·亞本維說,她是殖民聯盟的一名大使,也是我的上司。
「特萬指揮官,」我說,翻譯器替我翻譯,「我叫哈利·威爾遜。我是殖民防衛軍的一名中尉。要是你不介意,我想和你談一談。你可以用你的語言回答。我的腦伴會為我翻譯。」
「一方面我並不想說我不感謝你摘掉我脖子上的『刑具』;另一方面也請允許我說這是一個空洞的行為。不僅空洞,事實上毫無誠意。」
「我不想騙你,需要一段時間,」我說,「必須等我們結束目前這場衝突。在此之前,你將在我們這裏做客。」
「吃飯。」
但我的問題在於:我生活的時代特別有意思。
「導致一切的終結,」我說,「或者換個不那麼誇張的說法,殖民聯盟和種族聯合體兩者的分裂,所有種族回歸自己的一小塊空間,繼續彼此爭鬥不休。」
「我們的分析師同意前一點,但不怎麼同意后一點。然而,假如平衡者繼續進攻,隨著我們摧毀第二批目標,那就將成為現實。」
「我們有內線情報。」
「唉,中尉,」特萬說,「你不可能指望我會相信這種承諾也在你的許可權內吧?」
達昆退出對話。
「我們怎麼知道有哪些殖民星球意圖叛亂?」巴雅問。
「謝謝。中尉,我——我能和你開誠布公嗎?」
「我就希望你這麼說。但你記住,我知道的就是這些了。我不會隱瞞任何東西,但我知道的事情畢竟有限。」
「你的自由。」
「我沒有授權進行任何襲擊行動。」
「這我就說不準了,」巴雅說,「我認為喀土穆最近不會有人動任何歪念頭。」
「你不是真想談這個話題吧?」達昆說,「因為我有個好消息,朋友,你們並沒有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手畫腳的資格。」
「有道理。」
「除非平衡者還接觸了其他的殖民星球。」她說。
「什麼時候?」
我繼續向前走。哈特站在那兒,望著我走遠。
「不得不說,你比特萬指揮官更配合我們。」
我微笑道,「船長,問題不在於我是不是疑神疑鬼,而是宇宙一次又一次證實了我的懷疑。」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特萬指揮官看著我遞給他的列印稿說。我們又在先前那個房間里。實話實說,我有點看夠了這個房間。
我走進房間,勒雷伊戰俘正在等我。這個勒雷伊人沒有戴鐐銬,但頸部戴著一個電擊頸圈。動作超過隨意和輕鬆的範疇就會引來電擊,速度越快,電壓越高。
「所以特萬指揮官為什麼那麼做?」亞本維問,「為什麼進攻我們?」
「我不認為我們會成為朋友,非常抱歉。」
「但你藏了起來,」我說,「你和你的內閣。」
「中尉,假如你這些話里有個什麼道理,非常抱歉,我完全沒有聽懂。」
「我能理解。」
特萬什麼也沒說。
「想要的東西都得到了?」他問。
「那麼,說到哪兒了?」我說,「哦,對。我想和你談談。」
「對,」我說,「確實如此。我們知道喀土穆是打算共同宣布獨立的十顆殖民星球之一。平衡者說服他們當出頭鳥,從而實現它的目標。我認為這個目標有一部分就是讓我們作出過激的軍事響應。」
一小時后,我走出那個房間。哈特在等我,另有兩名防衛軍士兵在等著送特萬回禁閉室。
「解釋一下,中尉。」亞本維對我說。
「明白了。」
「還有其他工作可以做。」
「我不認為他會不同意,」我說,「他知道假如幫助我們,他的知識會被用來對付勒雷伊人。然而他還是幫助了我們,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也成了我的朋友。他是我認識的最了不起的人之一。我以認識他為榮。」
特萬指著脖子上的頸圈說:「我覺得那麼做對我恐怕沒什麼好處。」
亞本維望向我。我聳聳肩。
「對。」
「都是你的錯,」拉烏說,「你們人類,不是特指你。我們和你們的戰爭輸得很慘,尤其是曾經與我們結盟的奧賓人倒戈之後。那次我們失去了數個星球和權力,軍隊隨之縮減。很多士兵丟了工作。我是其中之一。」
「怎麼說?」亞本維問。
「是的,確實如此。不打破雞蛋就不可能做煎蛋卷,但上鍋前你必須搞清楚蛋里到底有什麼。」
「我衷心希望如此。」
「一個錯誤的規律。」
巴雅轉向我:「你一向這麼疑神疑鬼嗎?」
「我說過了,我對你和對特萬指揮官感興趣的東西不一樣。我認為你會非常有用。」
「你沒有被俘,」我說,「你死了。至少他們會這麼認為。你和其他所有的勒雷伊人,屍體損毀得無法辨認,而且根本沒有辨認的機會。你們在完成引誘殖民聯盟跳進陷阱這個目標時死去,現場布置得像是喀土穆星應該為襲擊負責。說起來,這一招挺損的。」
「我更喜歡能吃飽肚子。另外就像我說過的,我沒有什麼其他的選擇。」
「換取什麼?」
「很抱歉你失去了那些朋友。」
「哦,相信吧,」我說,抬頭對天花板說,「拉菲,你在聽嗎?」
「怎麼,你沒在外面錄像嗎?」
「你會殺死我們嗎?」科特林·塞·拉烏技|師問我。我們在先前我和特萬談話的那個房間里。房間重新布置過了。拉烏沒有戴電擊頸圈,他從一開始就沒有戴過。
「她是她。你是你。」
「也許你該再試試看。」
拉烏技|師做了個相當於聳肩的勒雷伊人動作:「在最近之前,這個組織一直很小,目標單一,去中心化。剛開始兩年,我甚至不知道還有一個更大的組織。我只和我所在的小隊一起出任務。」
「假如你們襲擊了第一批目標,平衡者繼續攻擊你們,那麼顯而易見的就是勒雷伊人並沒有資助我們。」
「人類不以對敵人心慈手軟而著名。」拉烏說。
「現在呢?」
「不。錢德勒號襲擊平衡者總部的時候,我在的小隊基本全滅。我能活下來是因為我被暫時借調去了另一個小隊訓練新人。襲擊后我留在那個小隊里,這個小隊由特萬指揮官率領,被你們殺了個乾淨。」
「不打算把東西裝回去嗎?」特萬指著桌上的電擊頸圈說。
「當然了,」我站起身,「你只需要記住有這個可能性。只要你願意。另一方面,請考慮一下我的請求。等你準備好開口了就告訴我。」我走向房門。
「有可能,」我承認道,「但我更願意認為還有其他的原因。」
「你按你們的年說,我自己換算。」
「你指的是監禁吧。」
「對,它確實取得了不少成果。」
亞本維大聲嘆息。
亞本維再次起身,這次的動作沒那麼誇張了。
特萬把列印稿還給我:「我不懂你們的語言,我不確定你為什麼會有興趣向我展示機密情報。」
「結局是不是一切的終結,這不是我此刻關心的問題,」巴雅說,「我關心的是平衡者接下來會做什麼,希望發生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