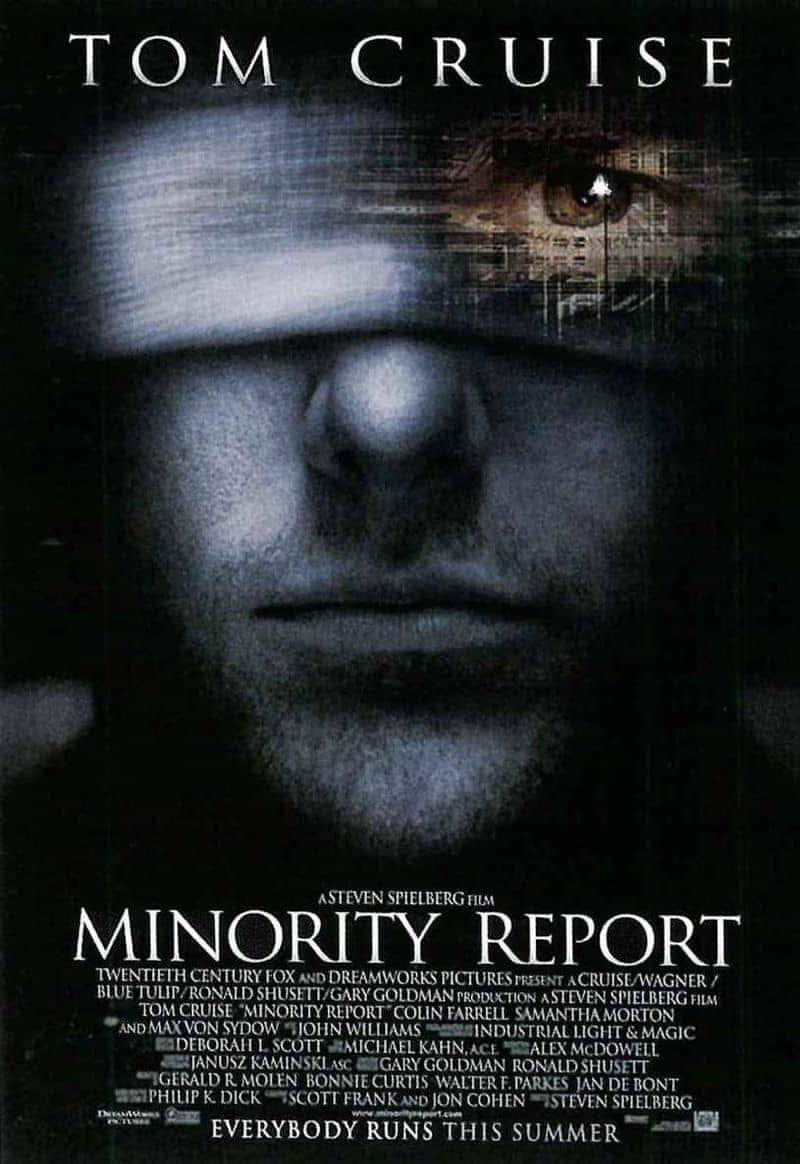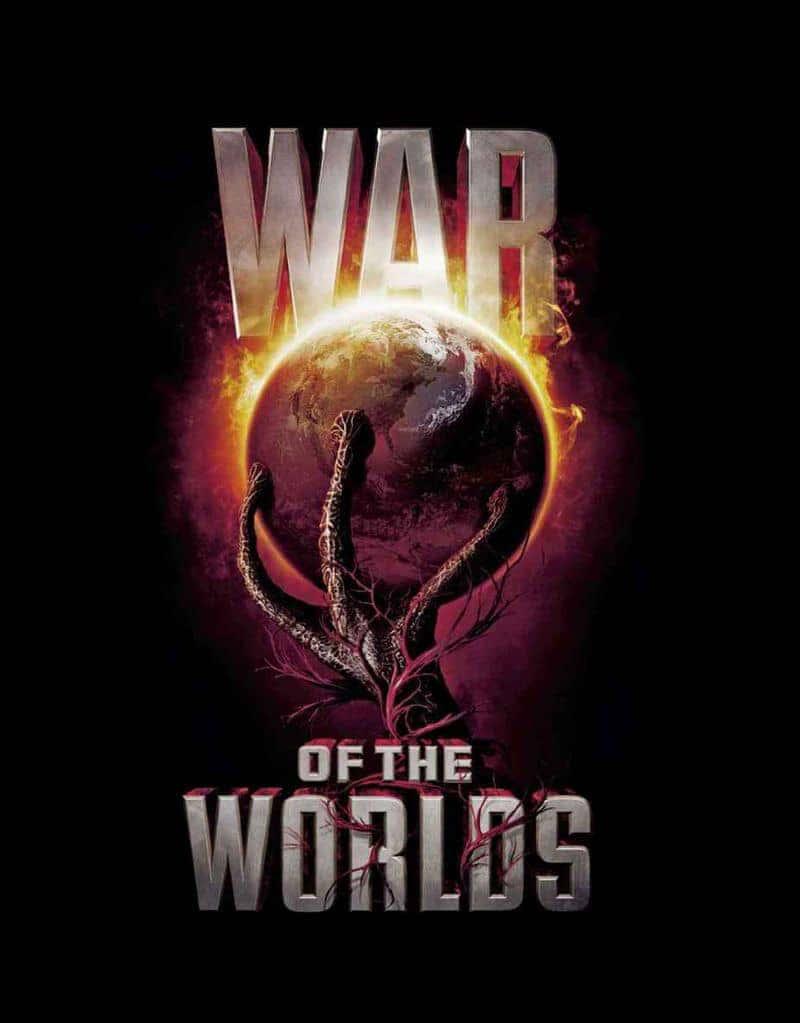詹姆斯·卡梅隆對話史蒂文·斯皮爾伯格
斯皮爾伯格:他之前不同意把影片命名為《人工智慧》,可還是……就這樣定了。他接著要求我去倫敦看他做好的那3000張分鏡表,我就立刻飛到了他的家裡,然後花了一兩天的時間與他一起把那些分鏡表過了一遍。那時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他的原話是:「我想這部電影現在的感覺更像是你的而不是我的,我正被其他的一些項目搞得有點心不在焉。」正是那個時候,他開始同意把這部電影叫作《人工智慧》。他說:「你有興趣執導這部電影嗎?我來做製片人。我會擔任執行製片人的工作,而你來做導演。」

《第三類接觸》中的一個場景,外星人歡迎地球人登上他們的母船。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
斯皮爾伯格:你說得對。我想《星球大戰》正位於《星際穿越》和《哈利·波特》之間。
卡梅隆:但這是在完全不同的場景中。
斯皮爾伯格:是用了不少時間來觀察天空。《E.T.》最初的暫定名稱就叫作《仰望天空》。這多少是借用了電影《怪形》中的最後一句台詞。我總仰望天空,這是受了我父親的影響,他還說,從上邊來的應該只有好東西。除了蘇聯(Soviet Union)發射的洲際導彈,也就剩下好東西才能克服我們的地心引力,從天空降臨。
卡梅隆:你的《大白鯊》(Jaws)可是把每個人都嚇得屁滾尿流的,不是嗎?你了解怪物,而外星人有時就是怪物,但也不總是。在拍《第三類接觸》的時候,你採用了另一種看外星人的視角。
斯皮爾伯格:是的,那是一場獅子座流星雨。我能記得這麼清楚,只因為之後過了好多年,我父親還在不斷提起,那次是獅子座流星雨!但我當時太小了。我們那時還住在新澤西州的卡姆登市(Camden),所以那就是說我當時是五歲左右。他半夜的時候叫醒了我——當時嚇著我了,因為天還沒亮,父親突然走進卧室里,對我說「跟我來」。如果你還是個孩子,這樣的事總讓你有點發毛!他帶我來到新澤西某處的一面山坡上,那裡有好幾百人躺在他們鋪著的野餐毯上。
卡梅隆:但是除了這個,這應該是收穫滿滿的一次合作吧?
斯皮爾伯格:哦,比那還要早很多,我就開始空想了。我畫了不少的草圖。都是些慘不忍睹的草圖,不過我以前就經常畫出很多嚇人的圖畫。
卡梅隆:它是在探究技術發展的意外後果,或為適應技術而改變的社會的意外後果。我們此刻正生活于這樣的一個世界。我認為我們正在與技術共同進化,我們正在改變它;它也在改變著我們,誰也不知道這場巨大的實驗將把我們帶往何處。
斯皮爾伯格:我們總是在這些問題上自尋煩惱,世界將去向何處?這個世界是不是就要毀滅了?不少科幻作品基本上都是在利用這樣一些恐懼,通過電影創作和故事敘述來告訴我們,怎樣才能阻止世界末日的發生呢?我們能否至少延緩一下世界末日的來臨呢?最好的科幻故事都是警世寓言。
卡梅隆:你之所以能執導這部電影,是因為……
斯皮爾伯格:還有《未來事物的樣子》(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里長著尾鰭的身體。後來卡迪拉克汽車倒是帶著尾鰭出廠了。
斯皮爾伯格:不能。而且一旦我們創造了核裂變,一旦我們分裂了原子,那我們就再也回不去了,不過它也可以被用在數不清的有益用途上。全世界都適用這樣一個道理,我們想出來的任何東西,它的用途都有好壞之分。
斯皮爾伯格:對我來說,去講一個反烏托邦故事就意味著我得丟掉所有的希望,我就得花上半年到一年的時間讓我的生活真正陷入一種消沉的狀態。我目前正在製作《頭號玩家》(Ready Player One),《頭號玩家》中的真實世界就是一個2045年的反烏托邦未來。但那個綠洲(OASIS),實際上是個供人們享受網路生活的虛擬世界,是一個你想是誰就是誰,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地方,你可以過上你夢寐以求的生活,這是我所做過的最接近反烏托邦的設定了。我不認為《少數派報告》是在講一個反烏托邦世界,《少數派報告》實際上是一個講意外後果的故事。它是一個道德訓誡,你在阻止未來的謀殺,然而證據卻來自三個占卜師或先知的預言,那麼對行兇者要施與什麼樣的裁決呢?把他們處以終身單獨拘禁——影片中叫「沉睡」——是否合適呢?這也是一出巨大的道德劇。
斯皮爾伯格:是必須得打敗。因此,赤色威脅(Red Menace)就是那顆狂暴的紅色行星。然後火星突然就一下子變成了敵人——而不是一個奇觀。我的父親正是帶我認識宇宙的領路人。是他用一套郵購來的愛特蒙特科學工具,製作了一架五厘米口徑的反射式望遠鏡——用上了一個人們通常用來卷毯子的大硬紙筒。他把這台望遠鏡組裝好以後,我觀測到了木星的衛星,那是他指給我的第一個天體。我還看到了土星和土星光環。這些事前前後後發生的時候,我大概六七歲。
斯皮爾伯格:還有能起皺褶的皮膚,皮膚下面的肌肉。肌肉在皮膚下面涌動。
斯皮爾伯格:那是我有幸製作過的最有意思的電影之一了。邁克爾·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那時剛構思出一個堪稱完美的概念,而他把這個想法透露給我的時候,我倆正在一起研究《急診室的故事》(E.R.)的第二版草稿。《急診室的故事》他是照著電影來寫的,我本來也要執導這部電影,但後來我們把它變成了一部電視劇。午休的時候,我問他接下來打算寫什麼書。他說他不能告訴我,我於是就反反覆復套他的話,直到他說:「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構思的主線。我在寫一本關於恐龍和DNA的書。」他肯說的就這麼多。我對他軟磨硬泡直到他答應把這本書的改編版權賣給我。

網飛(Netflix)的《怪奇物語》(Stranger Things)第二季發行的推廣海報。
Stranger Things © Netflix. Image courtesy of Photofest.
卡梅隆:我們都愛福里斯特。
卡梅隆:我還記得3年級的時候我看了那部《神秘島》(Mysterious Island)。我連忙跑回家裡,開始做我自己版本的《神秘島》。我想那就是一種創作的衝動,你認可了某種東西,轉回頭就想做出你自己版本的這種東西。
卡梅隆:或許是你童心在作怪,但你也熱衷技術。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被迫從一輛正在組裝的汽車裡出來……
斯皮爾伯格:我把它照搬過來了。我讓摩根·弗里曼通過旁白幫我交代了。
卡梅隆: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也曾說過類似的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更是坦言,完善了人工智慧的那個國家將統治世界。
卡梅隆:從《大白鯊》里的那個怪物,那個藏於水下你看不見的、巨大的未知恐懼,到像《第三類接觸》中的那些天使般的東西——你實際上是創造出了另一種有替代性的靈性,或有替代性的宗教。這種觀念認為,高於我們的東西將不會來自傳統上認為的地方,它將來自與一種無限優越的文明的接觸。
卡梅隆:但在最後我們總能打敗它們,這是在用我們的方式說,人類的聰明和勇氣將會戰勝那些由科學創造出來的怪物。這是我們把核戰夢魘擋在門外的一種方式。
《侏羅紀公園》這個故事之所以吸引我,也是出於人的傲慢之心,那種「如果這事有可能,為什麼不做呢」的感覺。小說中公園的創造者約翰·哈蒙德(John Hammond)無疑代表了一種經理人,一個馬戲團領班,他擁有的這個新時代的林林兄弟馬戲團(Ringling brothers)使一個物種得以復活。與此同時,他卻完全忽略了自己的所作所為將帶來的嚴重後果。與所有那些瘋狂科學家一樣,他的出發點是純粹的。他想成為沃爾特·迪士尼(Walt Disney),他要每個人都來看那些恐龍。當孩子們驚嘆于那些他們只能在故事書里看到的巨獸時,他要讓他們激動得熱淚盈眶。
斯皮爾伯格:那個地方也讓我很費解。但我認為令我驚嘆與折服的是,我竟如此迷戀阿瑟·C.克拉克和斯坦利·庫布里克的深度思考,或者他們想要的無論哪種象徵手法,或者他們在試圖賦予的深刻內涵,因此,他們的創作使我望塵莫及倒更好。它使我看到的東西顯然要多於我已經完全理解了的東西。
卡梅隆:是你把它定名為《人工智慧》,還是庫布里克事先就已經想好了?我們都知道他拍過一部關於人工智慧的經典巨作:《2001:太空漫遊》。
斯皮爾伯格:我相信在包羅萬象的宇宙某處,在包羅萬象的銀河系的某個地方,存在著由某種有機生物創建的高級文明,他們或許比我們先進得多,也或許比我們落後得多。我願意去相信它。我覺得我有資格親眼見到UFO,我拍過《E.T.》,拍過《第三類接觸》。我一直在等待著這樣一次目擊,但我從沒見過,儘管我遇到的說見過它的人已經有好幾百個了。
詹姆斯·卡梅隆:大部分我這個年紀還有比我年輕的電影人都會說,你是走在他們正前方的那個傢伙,是你讓他們熱血澎湃,讓他們產生了要做他們現在做著的事情的念頭。你創建了一個電影的幻境,我認為這以前並沒存在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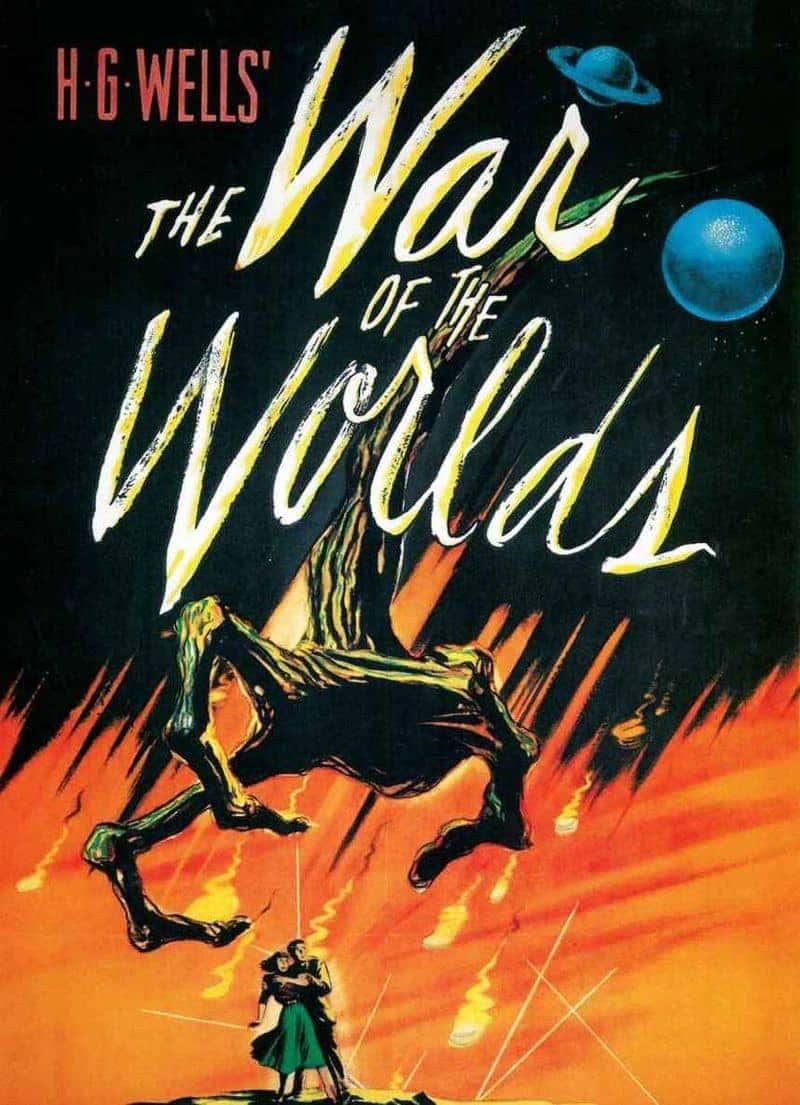
喬治·帕爾版《世界之戰》的電影海報,電影發行於1953年。
War of the Worlds © Paramount Pictures.

在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電影《人工智慧》(2001)中,海利·喬·奧斯蒙(Haley Joel Osment)扮演機器人男孩大衛。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Warner Bros. & DreamWorks. Image courtesy of Photofest.
斯皮爾伯格:是啊。做這事的時候總是得用鉛筆和紙,當然了,後來用到了8毫米電影攝影機。
斯皮爾伯格:邁克爾·克萊頓和大衛·凱普把所有那些東西都寫出來了,能在片場把這些都拍出來真是太棒了。
斯皮爾伯格:可是對於《人工智慧》這樣的影片來說,九-九-藏-書「恐怖谷」恰恰就是它最需要的東西。那是你竭力想得到的東西,你正努力找這種感覺,讓這個小孩身上存在某種類似機械的屬性,他也因此不是一個百分百的人類孩子。在影片中,海利·喬·奧斯蒙憑藉其非凡的演技與定力——除了電影的最後一個鏡頭,他在影片中一次眼睛也沒眨——僅僅化了一點妝、打了一點點粉,就能讓我相信他是一個機器人小孩。
斯皮爾伯格:啊,那些東西真是太棒了!那些邊緣閃著綠色光芒的飛船有點像是回飛鏢。這部電影對我來說也非常震撼。出於對喬治·帕爾的《世界之戰》的喜愛,我在《E.T.》中有一處向它致敬,《世界之戰》有這樣一個鏡頭,晚上他們待在一間農舍里,然後你看見了映在牆上的影子,突然,指端帶著吸盤的三根手指碰了一下安·羅賓遜(Ann Robinson)的肩膀。這一刻被我放進了影片《E.T.》里,埃利奧特聽見他窗戶外面有聲音,他很害怕並走到了窗戶邊,然後你就看到E.T.的手為了安慰他碰了他一下,這個安慰顯然對他起了作用。

斯皮爾伯格的《第三類接觸》(1977)中,外星人母船抵達地球。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 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
這就是我開始拍電影的原因。我的第一部電影實際上是《火車大劫難》(The Great Train Wreck),在那裡面我讓一列火車從左向右跑,而讓另一列火車從右向左跑。我把鏡頭正對著中間,讓它們在我的8毫米柯達攝影機前相撞了。孩子們天生就有創造出不存在的世界的能力,在實踐這種能力時他們就會做這樣的事。我們一開始就是講故事的好手,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一開始就是電影創作者。
斯皮爾伯格:是啊,超級機甲。機器實際上也在進化,機器造出更好的機器,然後這些機器再進化成更了不起的機器。
斯皮爾伯格:我想在這之前,他從未要求過任何人做類似這樣的事情。不過斯坦利和我都認識特里·塞梅爾(Terry Semel)和鮑勃·戴利(Bob Daly),他倆那時是華納兄弟(Warner Bros.)的負責人。我來導演,斯坦利做製片人是我們與華納達成的協議。這段經歷中的這一部分總讓我忍俊不禁——斯坦利說:「你是導演,我今後不會礙你的事。我們將來在一起就按著劇本來工作,而且我會是一個在英國工作的製片人,你只管在美國拍你的鏡頭。」他又補充道:「你需要安裝一台傳真機,因為我將來會給你發好多筆記、圖片和想法。而且傳真機得安在你的卧室里。」
斯皮爾伯格:在當時,我真正想做的是給我的鏡頭前打上儘可能多的背景光,好讓那些矮小的外星人變得幾乎像剪影一樣,這樣他們就可能會顯得更加表現主義。那時的服裝材質非常差,他們看起來就像是老版電影《豹人》(Cat People)里的樣子,後背上下都有拉鏈,在正面燈光下有些東西簡直就沒法拍。我認為,看到的東西越少,自己想象中的外星人形象就越豐富。我們可以把自己的面孔安上去。實際上我只允許亮出了一副外星人的面容,即普克的臉,那是特效美術師卡洛·蘭巴爾迪(Carlo Rambaldi)的創作。
卡梅隆:想想這部電影在當時是怎樣的驚艷。邁克爾寫這本書時,正值CG動畫開始縱橫天下的時候。我當時完成了《深淵》,完成了《終結者2》。為《深淵》和《終結者2》工作的大部分人都直接進入了《侏羅紀公園》的「猛禽」團隊和「霸王龍」團隊。還有他們已經率先嘗試的所有那些東西——那真是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是你讓這場雨下下來了,是你把那些數碼技術製作出來的、有軟組織和器官的角色呈現給大家,它們的眼睛會眨,看起來像真的一樣能分泌眼淚,甚至瞳孔還能放大。

在克里斯托弗·諾蘭執導的影片《星際穿越》(2014)中,馬修·麥康納飾演了宇宙飛船飛行員庫普。
Interstellar © Paramount Pictures. Image courtesy of Photofest.
斯皮爾伯格:正是。他說出了觀眾的心聲,生命總會找到出路,而且每一次他都是對的。我最喜歡的場景就是傑夫和扮演約翰的理查德·阿滕伯勒(Richard Attenborough)兩個人互相鬥嘴的那部分。
斯皮爾伯格:他們的作品是都發行在這一類雜誌上,而且很多作品都是樂觀主義的。它們不總是在計算我們離毀滅還有多遠,相反,它們總是在尋找打開視野、釋放我們想象力的方法,它們讓我們去夢想,讓我們去探索,讓我們犧牲小我成就大我。正是由於這些故事,再加上仰望天空,使我意識到,要是我什麼時候有機會拍一部科幻電影,我要讓那些傢伙是為和平而來。
卡梅隆:我也對這部電影產生過這樣一種強烈的生理反應。我彷彿體驗到墜入星際之門的感受,墜入了那種通往無限的通道。我來到陽光燦爛的影院外面,走在人行道上——當時看的日場——然後大吐特吐。說實話,它對我有一種生理上的影響。但我明白自己剛看了一部重要的傑作。14歲的我只能領會它其中的一部分,我能看懂骨頭變成了宇宙飛船,我甚至能看懂結尾部分的那個星際嬰兒,進化中的下一個階段。但我沒理解的是麗晶大酒店的房間。
卡梅隆:斯坦利避開了外星人可能會長成什麼樣子的這個麻煩,索性就不讓他們亮相了。你在《第三類接觸》中直面了這個挑戰,但我認為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做到了這一點。
斯皮爾伯格:我和編劇大衛·凱普(David Koepp)一起做的這事。大衛對這個有他真實的感受,對這種家庭有感受——這也與我的很多經歷產生了呼應,喚起了我這個離婚家庭長大的孩子的很多創痛。我還記得當我與大衛聚到一起時,我跟他說:「我們得把這個故事處理成在講一個單身父親,他實際上完全不關心自己的孩子,然而這次事件把他變成了一個關心自己的孩子勝過關心自己的人。」這個也成了《世界之戰》的核心。這部影片的結尾並不令人滿意,因為我怎麼都沒想出來該怎樣來結束那糟糕的事情。
卡梅隆:那時的人們都沉迷於迷|幻|葯中。在這部電影剛發行的頭幾年裡,我把它看了足有18遍——這還是在家庭錄像沒出現的時候,全都是在電影院里。我見過觀眾對它的各式各樣的反應,記得有個傢伙跑到過道里,衝著銀幕大聲尖叫「這就是上帝!這就是上帝!」那一刻他真是這麼想的。
斯皮爾伯格:做得糟透了。
卡梅隆:你忠實原著這點非常不錯。因為在伴隨我們長大的喬治·帕爾的那一版中,那些帶著力場的非常酷的反重力戰爭機械是漂浮在空中的。
卡梅隆:你讓一顆光點散開成了多個光點,然後掠過每個人身邊……
卡梅隆:我們再來說說怪物。在我們小的時候,最受歡迎的怪物就是恐龍,對吧?
卡梅隆:你的這種稍顯過分的推進,與傳奇的科幻作家兼編輯約翰·W.坎貝爾對科幻作品的處理手法如出一轍,他把科幻從那些搞硬技術的書獃子那裡向前推進了,之前,誰要想寫點科幻內容,非得拿個博士頭銜不可。原先故事里的那些隨處可見的方程、數學、物理學內容也慢慢演變成了更多的直指人心的人性故事。在我小時候讀過的那些科幻作品中,有能讓我感興趣的人物、能使我流眼淚的那些故事,它們的作者才是最好的科幻作家。我認為,即使在今天的好萊塢也仍然存在這樣一種感覺:科幻片算不上真正主流的電影藝術形式,因為它所講述的不完全是人與人之間的真實情感。我想這裏面有一個天大的謬誤,科幻是在討論人類的境況,我們雖然生活在一個技術世界里,但我們還是要站在人的角度上來處理它。
斯皮爾伯格:摩根總把任何事都變得順耳。
卡梅隆:那一定把人們都驚呆了。
卡梅隆:但你也創作出了E.T.這樣一個深得人心的角色。在有關外星人的創意中,有一件事情讓我非常著迷,那就是它們的長相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們要怎樣與它們交流,或我們要對它們做出怎樣的反應。你給他配上了一雙大大的眼睛,人們對一對大眼睛會做出很本能的友善的反應,因為嬰兒擁有一對大眼睛。
卡梅隆:它就像是一張羅夏墨跡圖(Rorschach),你把自己完全陷進去了。
卡梅隆:傑夫·高布倫(Jeff Goldblum),這樣一位令人矚目的具有良知的人物說,「自然將會找到出路」。
卡梅隆:他讓我們一睹了那些正面未來世界的崢嶸,但其中也不乏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存在,這一點很有意思。你還拍過某個東西——我甚至都不知道該把它歸到哪一種類型里——那就是《少數派報告》。它有那麼一點兒像是個時間旅行故事,因為你預見到未來,但又依據未來的結果返回當前探尋成因,並對其進行干預。
斯皮爾伯格:一點沒錯。那能夠擊敗任何有敵意的威脅。你可以把50年代的大部分科幻片的結尾與40年代和50年代的約翰·韋恩(John Wayne)的大部分二戰片畫上等號。
卡梅隆:我認為只借鑒其他電影的電影就是最糟的電影。最好的電影會想辦法把你與你的經歷與體驗鮮活地聯繫起來。
斯皮爾伯格:人們之所以感到震驚,是因為那人竟然消失在銀幕里了!在星際之門出現時。
斯皮爾伯格:正是。這是最讓觀眾興奮的地方,因為觀眾就想看看哪裡會出錯。誰會關心做對了的事情呢?
斯皮爾伯格:在這方面他就是一個夢想家,他還一直在讀《類比》雜誌。是那些廉價本吧?還有《驚奇故事》(Amazing Stories),廉價本的那種。我以前常和他一起讀那些雜誌。有時,他會在晚上讀那些書給我聽,也會給我讀那些小報。
斯皮爾伯格:我正是這麼考慮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起先把《E.T.》的劇本交給了哥倫比亞電影公司(Columbia Pictures)。我當時想在他們投資讓我拍《第三類接觸》之後,這部電影就算我還他們的人情。我當時認為,我是不會帶著一個講外星人的劇本跑去找環球製片九-九-藏-書廠(Universal Studios)的。所以,我帶著劇本去了哥倫比亞,但他們拒絕了,我就轉頭把它交給了環球。
卡梅隆:嗯,的確非常近了。有意思的是,我們所挑選出的技術形式,通信技術形式,是打包定向傳輸,為的就是我們能修改我們所說出的話,而且也不用非得實時回復。對我的孩子們來說,對著話筒講話是一種匪夷所思的概念,因為回頭你得為你剛才所說的內容負責,你所做出的任何陳述的後果已經在你做陳述的過程中被分離出來了。這就是互聯網以及所有那些先進的通信技術為我們帶來的變化。在社會交際方面,我們也正在改變。我們實際上正生活在科幻中,而我們這些科幻電影創作者不得不跑著追趕這個現實世界。
我的父母覺得電視——這得說回20世紀50年代早期了——對任何孩子來說都是一種最糟糕的影響。我不知道在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發表相關研究成果之前,他們是如何知道這個的,可他們像是預知了一樣,所以他們不讓我看電視。我僅僅能看少數節目,比如,傑基·格黎森(Jackie Gleason)的電影《蜜月期》(The Honeymooners),或席德·西澤(Sid Caesar)的《你的秀中秀》(Your Show of Shows),但我不能看《法網》(Dragnet)或《M小組》,或當時那些非常酷的偵探連續劇中的任何一部。

《怪獸王哥斯拉》(Godzilla, King of the Monsters! 1956)的電影宣傳海報。
Godzilla, King of the Monsters! © Embassy Pictures Corporation. Image courtesy of Photofest.
卡梅隆:你是在對這個世界進行處理——使其以某種視覺形式的東西還原。
斯皮爾伯格:我想,對我來說是我第一次在電影院里看《飛碟入侵地球》(Earth vs. the Flying Saucers)的時候,你看不清那些飛碟里的人,因為他們的臉上都罩著一個巨大的面具,並與他們身上的那套護甲連成了一體——在一個場景里,其中有一個士兵向著一個地外生物開了槍,然後他們摘掉下了那個外星人的面具,我被我看到的那張臉給嚇壞了。我也做了同樣的事情,一回到家裡,我就開始一遍又一遍地畫那張臉——不是為了使自己平靜下來,而是要把那張臉畫得比那部電影里的還要嚇人。我會把它畫到比嚇到我的那個臉的樣子更嚇人。
斯皮爾伯格:是這樣的。從《大白鯊》技術方面的手忙腳亂中——在真正的大西洋上拍這樣一部電影是不可能的。頭腦健全的人都會把它放到一個大鐵箱中拍攝,而今天的人們可以用CG動畫來處理它,他們會在一台計算機上來製作它。但我卻喜歡在海上,我比較喜歡實景拍攝。然而那卻是一次糟透了的經歷,我當時正在斷送掉自己的前程。人人都在告訴我這樣做會斷送掉自己的前程,我信他們,因為我每天只能拍一到兩個鏡頭。
斯皮爾伯格:我也這樣認為。在《機器人啟示錄》(Robopocalyspe)這個作品上我已經花了很多年時間了。因為這個故事就是在講一個有著最深刻知覺的人類染色體,從根本上他要比人類聰明得多,所以想從人類手中奪取控制權,掌管這個世界——有一點點像是《兩隻老鼠打天下》(Pinky and The Brain)的成人版本,但它比較嚇人。埃隆·馬斯克進一步預言,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會是一場核毀滅,它將會是一種機械對地球的接管。
斯皮爾伯格:這是一次棒極了的合作。我從斯坦利那裡收到了那麼多的筆記,那裡面有關於鏡頭角度的筆記、有關於工藝的筆記,有頁筆記寫著:「你打算怎樣塑造大衛(大衛是電影中的主角機器人男孩)這個形象?我認為大衛應該是一個機器人,他不應該是一堆假體材料,他應該是台機器。」工業光魔(Industrial Light& Magic)公司的金牌特效師丹尼斯·穆倫(Dennis Muren)飛到英國,與斯坦利討論了很久如何用電線做出一個真正能動的機器人男孩——就像E.T.和普克。我想,斯坦利曾為此做了一些試驗,這都發生在我接手這個故事之前。斯坦利發現,要使用一個機械男孩的話這事就做不了,這還是在全計算機生成真實感動畫角色首次出現在電影中之前,第一次出現是在《少年福爾摩斯》(Young Sherlock Holmes)中,更在《侏羅紀公園》之前。要是放在今天,斯坦利一定會把大衛做成一個實景背景中的數字角色,毫無疑問。
斯皮爾伯格:斯坦利·庫布里克。我認識斯坦利是從我製作《奪寶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那時候開始的。我在《閃靈》(The Shining)的拍攝外景地遇到了他,那時他剛完成「遠望酒店」的搭建工作,我們也正打算在那裡搭建「靈魂之井」的外景。我去位於博勒姆伍德(Borehamwood)的埃爾斯特里製片廠(Elstree Studios)考察,他們告訴我說斯坦利·庫布里克正在使用外景地,我不能再使用了,因為那裡已經被封閉了。我問他們的製片人,我想那會兒是道格·特威弟(Doug Twiddy)吧。「我能見一下斯坦利·庫布里克嗎?」他非常熱情,說,「可以,請過來吧。」我就在那天見到了斯坦利,然後當天晚上他又邀請我去了他家。那還是在80年代。我們19年的友誼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順便說下,多數時候都是通過電話聯絡。

斯皮爾伯格執導的電影《世界之戰》中的三腳怪物襲擊。
War of the Worlds © Paramount Pictures. Image courtesy of Photofest.
卡梅隆:你我都與世界上最好的數碼藝術家在一起合作,我們也都知道,目前還沒有什麼東西是我們能想象得出,而他們做不出來的。如此說來,這就變成了一個藝術家的選擇問題。我做什麼,以及我希望自己做什麼,都總是在拼想象,僅憑思考是無法完成的。
卡梅隆:正是在那之後,CG技術的革命才鋒芒畢露。
斯皮爾伯格:這有點令人毛骨悚然,因為這幾乎是在說,某樣比我們聰明、並且下棋也能下過我們的東西,要把這個世界當成一個棋盤,而且還要將我們的軍,使我們徹底滅亡。我不知道我對這種事的相信程度能否達到50%,因為我生來就不太相信這類事情。我總認為,不管用什麼辦法,我們將來一定會找到一條出路,擺脫掉我們給自己設定的每一個困局。我們都有同理心,儘管我們平時極少聆聽它的聲音,或者將它表現在外。但每個人都有這種能力,而正是這種能力,我相信,總會把我們從邊緣上拉回來。
卡梅隆:鏡頭切換到幾十年以後,你在《侏羅紀公園》中與世界頂級的古生物學家們在一起工作了。
斯皮爾伯格:這類題材很容易被拔高評價,但我不敢自誇崇高。我不得不承認推出《劫持》的初衷就是為了佔領市場,努力抓住我所能吸引到的最大數量的觀眾——把那些外星人設定得陰險又充滿敵意,他們能進入你的大腦,給你留下你的母親被傷害的記憶,用這個辦法迫使士兵扔掉他手中的武器,然後再把他重塑成一個無害的人。
斯皮爾伯格:一點沒錯。當我坐下來畫分鏡表時,在處理那些草圖的過程中,最好的創意就都出現了。這些點子事先沒在劇本里,甚至都不在我之前的想象里,實際上就是在我繪圖的過程中,它們一下子就出來了。我畫得越多,這樣的點子也就越多,我想《少數派報告》中的所有場景都來自我繪製分鏡表的過程。我們原來的劇本中也有不少東西,但更多的是來自分鏡表。
卡梅隆:你是從《大白鯊》中學會的這個嗎?人們看到得越少,效果反倒更好。
斯皮爾伯格:但它們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全部是建立在數學運算基礎上的,是建立在假設上的,是建立在數學方程式的經驗上的。我們的卻是來自一個被稱為靈魂的地方,來自一個無法形容的地方。我相信那個地方的事物超越了我們的知識,甚至超越了我們的理解力。有時,對我的孩子們說說這話還是挺有好處的——你們還是得有一點點信念。
斯皮爾伯格:我想這一切都開始於在廣島(Hiroshima)和長崎(Nagasaki)的那兩次原子彈爆炸。
卡梅隆:可是它們好像和我們一樣有人性,至少和我們一樣有同理心和同情心。它們非常同情大衛。
卡梅隆:但這對你有好處。
卡梅隆:是不是德魯·巴里摩爾先發出了尖叫?然後E.T.也跟著尖叫了起來。這是電影史上最滑稽的瞬間之一。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總得有個傢伙走在我們大夥前面吧。走在我前面的有一大群傢伙呢。喬治·帕爾、斯坦利·庫布里克、威利斯·奧布萊恩(Willis O'Brien)。我認為在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激發我想象力的其實就是恐懼。我得做點什麼來擋住那些讓我害怕的東西,天黑以後,幾乎沒有什麼不讓我害怕的。
卡梅隆:我想H.G.威爾斯也沒能把它想出來。索性讓一場普通感冒了結了那幫壞傢伙。
卡梅隆:因為他不坐飛機。(庫布里克有飛行恐懼症。)
我問:「為什麼?」他回答:「因為萬一有人進來,看見了我寫給你的東西怎麼辦?它必須安在一個私密的地方。你得向我保證它會安在卧室里。」就這樣,我把傳真機放進了我的卧室。但你知道傳真機的鈴聲有多響嗎?它是普通座機電話鈴聲音量的10倍。而且在凌晨2點這東西突然發作時。我的老……
卡梅隆:是的。兩者中有那種被侵害的感覺,那種無助的感覺。但你想辦法把它變成了一個家庭故事,用家庭把所有人都聯繫到了一起。
卡梅隆:的確非常令人信服。這麼說,你那時正努力創造著「恐怖谷」。
斯皮爾伯格:好處就是使我變得頑強了。我並不是要拿點什麼來向別人證明,而是向我自己,不過我後來沒被解僱,而且我也沒搞砸。如果觀眾不買賬的話,它或許會使我身敗名裂,但我絕不會輕易放棄它。
卡梅隆:克里斯·諾蘭對《星際穿越》所做的那些處理是諮詢過專家的,他找到基普·索恩(Kip Thorne)這樣的科學家,問「黑洞是什麼?它實際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我們想把這類東西給展示出來」。後來他又找很多航天推進和生命保障方面的專家進行交流,最後他製作出了看起來還算可信的航天飛行器和行星表面。他沒有給那個行星安排許多有趣的外星人居住。那兒只有嚴峻的生存難題,它需要人們用智慧和知識去應對。但即使是諾蘭,在電影的結尾處也變得有點超然和靈性了。
卡梅隆:在涉及與地外生命首次接觸方面,你已經完成了兩部影響深遠、令人驚嘆的電影。顯然是《第三類接觸》促成了《E.T.https://read.99csw.com》的誕生,我認為它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第三類接觸》的續集,但故事更加註重個人。
斯皮爾伯格:我認為它如果不是「恐怖谷」,後面它就起不了作用。裘德·洛(Jude Law)也一樣,裘德·洛必須看起來像個「恐怖谷」——部分是人類,也有某種合成的東西。或者說是一個幻影。
斯皮爾伯格:《星球大戰》,在喬治·盧卡斯的《星球大戰前傳2:克隆人的進攻》里,所有那些飛行器就都帶有這種風格,跟《未來事物的樣子》有點類似。

在《E.T.外星人》中,埃利奧特(亨利·托馬斯飾)和E.T.竭力躲避兇惡的政府爪牙的追捕。
E.T. the Extra-Terrestrial © Universal Pictures. Image courtesy of Photofest
卡梅隆:諷刺的是,我發現科幻作品在預言未來方面實際做得並不怎麼好。

格蒂(德魯·巴里摩爾飾)在親吻可愛的外星人E.T.。
E.T. the Extra-Terrestrial © Universal Pictures. Image courtesy of Photofest.
斯皮爾伯格:那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時機,就像你剛才所說的,那本書、那種構思出來的時間點正巧趕上了數碼時代的黎明時刻,這兩者交匯在一起為我們提供了有利條件。我們才有可能真的創作出第一批數碼電影的主角和明星。你得明白,在《侏羅紀公園》中只有59個數碼恐龍的鏡頭,斯坦·溫斯頓(Stan Winston)當時做了一個全尺寸的三角龍,他還做了一個全尺寸的霸王龍,以及一個全尺寸的腕龍的頭和脖子。這部電影的成功實際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斯坦。我認為斯坦·溫斯頓——在未來,人們回顧他時,對他的評價將不亞於威利斯·奧布萊恩和《金剛》(King Kong)。他真是這世界上最親切的傢伙。
卡梅隆:你要知道它們會儘可能地離你遠遠的,因為傳言說你其實是一個外星人入侵的先驅,他們不想讓這個傳言成真。你知道這個說法吧,他們說這幾十年以來,你一直都在故意讓人類放鬆警惕。
卡梅隆:在續集電影《失落的世界》中,你又把這個給保留下來了。
斯皮爾伯格:有一天我曾問了史蒂芬·霍金這個問題,那時《回到未來》剛剛上映。史蒂芬·霍金說進入未來是非常有可能的,但回到過去是不可能的。他當時是在繞開那個話題,其實是說《回到未來》中的一切都是永遠不可能發生的。我對時間旅行思考得不是很多,我們不是已經有那麼多的相冊了嘛,記憶是我的時間穿梭機器。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那無與倫比的職業生涯已跨過了50個年頭,涵蓋了你能想象到的每一種類型片,但唯有科幻片是這位導演最頻繁光顧的一種電影類型,由他所打造出的引人入勝的現代經典有:《第三類接觸》《E.T.》《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1993)及其續集《失落的世界》(The Lost World: Jurassic Park, 1997)、《人工智慧》(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01)、《少數派報告》(Minority Report,2002),以及《世界之戰》。他最新一部令人眼花繚亂的故事片,改編自歐內斯特·克萊因(Ernest Cline)的暢銷小說《頭號玩家》(Ready Player One),這部電影將會在大銀幕上描繪出一個全新的虛擬世界——一個與我們的世界幾乎一模一樣的世界。在這場話題廣泛的談話中,斯皮爾伯格與詹姆斯·卡梅隆一起討論了斯坦利·庫布里克(恢宏巨制《2001:太空漫遊》的電影創作者,后與斯皮爾伯格結為密友知己)所開創的傳統,也談到人工智慧所帶來的種種危險,以及從童年時代起就一直在激勵著這位作家、導演、製片人產生無限想象能力的那些恐懼。
卡梅隆:於是你著手拍了一部電影短片?

出自影片《E.T.》的標誌性畫面,一輛飛起的自行車在月亮背景下襯托出的剪影。它後來成了斯皮爾伯格的製片公司,安培林合伙人(Amblin Partners)的標識。
E.T. the ExtraTerrestrial © Universal Pictures. Image courtesy of Photofest.
斯皮爾伯格:即使在科幻作品還沒有變得流行以前,我們還有格林童話故事。你要嚇唬你的孩子去做正確的事情,嚇唬他們不要犯錯誤。要是你咬手指甲,就會有一個傢伙拿著大樹籬剪跳過樹籬叢,然後剪掉你的手指。記得在我8歲大的時候,在大人給我看的一本帶插圖的書里,有個畫面就是被切斷的手指在往外噴血。
卡梅隆:摩根·弗里曼的聲音能讓任何事都聽起來有道理。
斯皮爾伯格:我們甚至在繪圖板上都沒勾勒出的未來,微軟和蘋果就已經替我們想出了方案,相反的情況很難去想象。他們正在研發一些特別的產品,那些我們在熒幕上還沒有被實現而僅存在於夢想中的東西。可以說,這直接導致了《人工智慧》的誕生。
卡梅隆:那是一種核毀滅與共產主義混雜在一起的東西,而且也得被徹底打敗。
卡梅隆:縱觀你擔任導演和製作人的所有作品,你已經拍過很多有關第一類接觸或外星人入侵的影片,以及類似的主題——《劫持》(Taken,2002年的一部電視迷你劇)和《隕落星辰》(Falling Skies)。這是出自於你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注嗎?你已經拍過那麼多的二戰題材,而二戰感覺就像是被外星人入侵。
卡梅隆:但他們仍然是一些令人同情的角色。為什麼會這樣?我們為什麼不僅給一台機器輸入了意識,而且還輸入了能讓我們產生好感的東西?我們能贊同這樣做嗎?
卡梅隆:就像《西部世界》(Westworld)的海報上所說的:哪個地方會出錯?
斯皮爾伯格:這樣的惡魔我還有不少呢。
卡梅隆:他像一個夢想家。
斯皮爾伯格:有過,我被那東西嚇過。我還被《小鹿斑比》(Bambi)里的森林大火給嚇過,那場火帶給我的驚嚇要勝過《幻想曲》(Fantasia)中那個從山裡跑出來的魔鬼。但我認為,我的父母在做他們認為是正確的事情的時候,我有點傳媒營養不良了,也正因為如此,我開始想象我自己的節目。既然看不了電視,不如索性給自己虛構點什麼東西出來,好讓自己樂呵一下。
斯皮爾伯格:我總認為《少數派報告》應該歸到菲利普·馬洛(Philip Marlowe)或雷蒙德·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那一類偵探故事里……薩姆·斯佩德(Sam Spade),以及約翰·休斯頓(John Huston)所有的那些了不起的電影,例如《馬爾他之鷹》(The Maltese Falcon)。但這部影片是一個通靈偵探故事。
卡梅隆:科幻作品倒是經常涉及信念以及靈性方面的話題,你不認為這很有趣嗎?科幻是講述科技及其對我們的影響的,結果發現科技也經常「撞南牆」,科學也存在一個局限。
斯皮爾伯格:是的。一種無限優越的文明將會找出你身上最好的東西,而你也會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現出來,正如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所說的「你本性中的善良天使」,這就是善的作用。善不會滋生出惡;善只會孕育出更偉大的善。而我認為這就是我心中最好的科幻作品的作用。
斯皮爾伯格:確實如此。現在的科幻作品不可否認地成了一道主菜,儘管之前它曾是餐后的甜點。如今,你會先吃甜點。現在正在賺大錢的電影都是藉助光學,讓我們暫時放下懷疑,轉而沉浸在蝙蝠俠、超人、神奇女俠、托爾和復讎者聯盟的世界里。我的確有種非常強烈的感受,這些都還不是主菜,除非它能把人類境況、像你我一樣真實鮮明的人物角色,以及生活在今天這個世界里的人們作為立足點。否則,它就只是你用數字工具製作出來的一道亮麗的風景,而不是你能用敘事做出來的東西。
斯皮爾伯格:一點都不好玩。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懸念的時候我還是個小孩——來自父母允許我去電影院看的所有的迪士尼電影。但第一次讓我真正體驗到懸念時我還非常小,我看了一部電影,那部影片是重映的,名字叫《登陸月球》,又是一部「喬治·帕爾」電影。當電影中的首次登月之旅著陸后,他們卻沒法離開月球了,除非他們從飛船里扔掉好幾噸重的載重,我記得還是孩子的我都沒法在座位上坐得住了,我記得我幾乎感覺都要吐了。我並沒意識到緊張感已從腹中湧起,然後爬到喉嚨,最後化作尖叫噴涌而出。
卡梅隆:如此來說,你已經拍過那種超然的、精神層面上的第一類接觸了,那是對未知所能提供的東西的一場禮讚。後來,你九九藏書又拍了《世界之戰》。
斯皮爾伯格:他們都尖叫了起來。德魯還不斷在說,「我能再尖叫一次嗎」?這的確很有趣。
卡梅隆:下面的問題我也就不兜圈子了。根據你的經歷和世界觀,你認為外星人是否存在?你相信他們已經來過地球了嗎?
卡梅隆:艾薩克·阿西莫夫、羅伯特·A.海因萊因,所有這些傢伙的作品都是發行在這些廉價雜誌上的。
卡梅隆:讓我們從積極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吧。如果這是一個成功的策略,那它是因為,作為一個群體,我們渴望把我們的噩夢放大書寫在大銀幕或小熒屏上。在我來看,這似乎是科幻作品的一項重要本質。它是在利用我們早在兩萬年或五萬年前就已經有的,對森林里的野獸的那種恐懼,然後讓我們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重新來感受它。
卡梅隆:然後你真的就這麼做了。你父親曾有一次帶著你去看流星雨,是嗎?
最近和一些人工智慧專家交談時,他們真的讓我想起了20世紀30年代的原子能科學家,那些人當時就相信,他們正在為未來創造一個無限的能量之源。這就好比,你沒有意識到一旦你把牙膏從管子擠出來了,你還能把它給弄回去嗎?
最先受到真正意義上影響的是日本人。東寶(Toho)出品的《哥斯拉》(Godzilla)(1954)當然是第一個真正利用了那種文化上和民族上的恐懼的電影,那種恐懼已經籠罩了那個國家。從核爆的那一刻起,不管任何東西,是從東京灣里鑽出來的也好,還是從夜空中降落下來的也好,都是侵略性的、不懷好意的,而且是不留活口。我打小就給自己灌輸這類東西,我看過所有的B級恐怖片,我看過所有的藝盟(Allied Artists)的恐怖片,我看過莫諾格雷姆(Monogram)的恐怖片,我看過漢默(Hammer)的電影。全都看過。然後我發現要找出一個正派的外星人,好讓我能產生與他或她進行交往的想法,是根本不可能的。所有外星人都想方設法要毀滅人類。
卡梅隆:事情照常運轉了就沒有趣味了。
卡梅隆:你好像是被科幻中的奇觀、神秘、夢幻和令人敬畏的東西給吸引住了,但吸引你的也有強烈的社會原因,以及一些體現社會重要性的事物。我好奇的是,為什麼你從來沒有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塑造一種反烏托邦的科幻未來,就像《一九八四》。
斯皮爾伯格:是這樣的。馬修·麥康納(Matthew McConaughey)變成了一個幽靈。他變成了一個有科學根據的幽靈。
卡梅隆:對一個科幻作家來說,這很好解決。地球曾經是UFO最熱門的一個旅遊觀光地……後來它們意識到,它們被拍在照片里的次數實在是太多了。我卻認為它們是來自未來世界的密使,試圖在事情被我們嚴重搞砸之前把它們給修正過來,它們會帶著我做時間旅行。你的作品差不多已經把科幻里的每一個類型都嘗試了——接觸外星人、太空旅行等每一樣東西——而且你還是《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系列電影的執行監製。所以,你認為時間旅行是可能的嗎?
卡梅隆:我也是。一年級時,我想成為一個古生物學家。剛才那個恐怕也是我學會的第一個長單詞了。後來我卻發現恐龍都已經滅絕了,想象一下我有多失望。
斯皮爾伯格:在我們講這些故事時,我們一般會試著做點什麼呢?我一般會先去試著觸動人們的心靈,而不是直接給他們交代故事,我總是想先抓住人們的心。當然了,有時奔著心靈去的事情做得太多了,難免會被人詬病為多愁善感。對此我倒是不太在意,因為……有時我需要推進得稍過分一點,這樣我對這個社會的影響才能稍稍深入一點。比起我年輕時初入影業的那個時期,當今這個社會的「多愁善感」有一點欠缺了。
斯皮爾伯格:我聽說過這個傳言的事,太離譜了。你知道,我會躲開鯊魚,但我並不想躲開UFO,直到現在,我都沒有過目睹UFO的經歷。我並不是說眼見就一定為實,但我現在的感覺是……為什麼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甚至追溯到60年代末,有那麼多的UFO被相機拍到,而現在卻少得多呢?現在就是沒有人能用什麼設備把一個UFO目擊事件給記錄下來。
卡梅隆:作為一個無神論者,這個場景會讓我大笑。但我想若是有人是信徒的話,他或許對此有他另外的一番看法。
斯皮爾伯格:最頂級的收藏品!我們愛福里斯特。他在科幻和奇幻之間做了非常嚴格的界定。奇幻是《哈利·波特》(Harry Potter),而科幻是《星球大戰》。
卡梅隆:我是對比著早期的原子能來思考人工智慧的,它們都有著那種能量無限的願景,它們都能推動這個世界,它們能創造出核能飛行器,它們能進入太空。可是,它們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炸掉兩座日本的城市。
卡梅隆:他應該是剛起床,對嗎?在英國?
斯皮爾伯格:而且我去英國的次數也不多。只要我在英國,我就會去看他,但主要還是在電話上聯絡。我們在電話上的那種馬拉松式的談話真能持續八到九個小時。毫不誇張,吃午飯和晚飯都不掛電話,就我倆一直說話。他從沒邀請過我加入他的創作圈子裡去,直到有一天他說,「我想讓你看點東西」。這是何等的榮幸,這人可是拍過《2001:太空漫遊》的,更別提還有《殺手》(The Killing)、《殺手之吻》(Killer's Kiss)、《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洛麗塔》(Lolita),以及《巴里·林登》(Barry Lyndon)。現在這個傢伙請我看他寫出來的某個東西,因為他想讓我去找一個作家,好把它改編成劇本形式。他給我寄來了布賴恩·奧爾迪斯寫的短篇小說《整個夏天的超級玩具》(Super-Toys Last All Summer Long),斯坦利要求我在看這個故事之前,先看他和伊恩·沃森(Ian Watson)基於布賴恩·奧爾迪斯這個短篇小說所寫的,一本長達79頁的電影大綱。
斯皮爾伯格:《怪奇物語》就做得非常好。《怪奇物語》是一部純科幻的電視劇,它提及了你、我,以及別的一些人所拍過的很多電影,但它把這個處理得非常特別,它可以說是一部集大成的優秀作品,但從頭至尾又只講一件事。你會愛上那些孩子,不想有任何不好的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怪奇物語》中所有那些天才的想象都是關於這些角色的。
卡梅隆:像《E.T.》一樣,你採用了很多第一類接觸的主題,而且我得說,你恰到好處地把它處理成了以家庭為中心,或以孩子為中心的電影。
斯皮爾伯格:因為這個故事的講述者就是12歲的我,我是在為我自己拍這部電影。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這種有趣的東西在我的生活中是匱乏的,沒有太多這樣的故事能讓我盡興。而且那個時代還沒有恐龍玩具,你無法滿足你對一個已經消失了的物種的求知慾,因為商店裡根本就不賣這些東西。
卡梅隆:誰都沒預言出互聯網。
斯皮爾伯格:我們的確只能這樣做了。一直以來。在每一個項目上,這都是最難去做的一件事。要想出一個原創故事很難,同意這種看法的作家一定不在少數,想出原創故事是一件很難的事。想出某樣東西,而這樣東西又不能讓人立刻把它拿來與他們之前看過的電影中的其他東西做比較,也不能帶有一點點先例,這非常難,因為我們正站在以各式各樣風格敘事的巨匠的肩膀上。
斯皮爾伯格:凌晨2點,我這兒還是半夜呢,但他那兒是白天。那東西會在凌晨1點、3點、4點發作。這種情況持續了兩個晚上,然後我的妻子,凱特·卡普肖(Kate Capshaw)把傳真機從卧室里扔了出去,並且說:「你必須對斯坦利實話實說。告訴他所發生的事。」我打電話給斯坦利,告訴他都發生了什麼。
斯皮爾伯格:說到這我們又得重提一下喬治·帕爾那一版的《世界之戰》了。影片的結尾是在一座教堂里,女主角的神父向著那些已經降落的圓筒中的一個走去,他拿著一個十字架,他還拿著一本《聖經》,然後他被焚化了,他被徹底燒成了灰燼。
斯皮爾伯格:我落入他倆的電影創作和概念合作之間的裂縫裡了,而落入這樣的裂縫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我所墜入的裂縫就是那個星際之門。我認為我們都曾掉進了這同一座星際之門,然後從另一頭出來,開始創作電影。
但要記得,我們必須把科幻與奇幻分開來看。你知道的,我過去常去買福里斯特·J.阿克曼(Forrest J.Ackerman)的雜誌《電影世界的著名怪物》(Famous Monsters of Filmland)。
卡梅隆:我倒是傾向於這裏面有個比較複雜的坐標範圍,你可以把《火星救援》(The Martian)、《星際穿越》(Interstellar)和《2001:太空漫遊》放在硬科幻、硬技術那一頭的坐標範圍里,然後可以把《星球大戰》放到距離奇幻這一頭比較近的坐標範圍里,因為它裏面有光劍和巫師諸如此類的東西,而科技框架只不過是它披著的一件外衣。如果你跨過了中間的那個坐標點,點那邊就再也沒有科學,完全只剩下魔法了,我認為這時你就進入《哈利·波特》和《指環王》(The Lord of the Rings)了。
卡梅隆:他利用科學創作出了某種有關來世的情節,這很有意思。
斯皮爾伯格:我學會的第一個字母很多的詞彙就是「腫頭龍」(pachycephalosaurus)。接下來就是「劍龍」(Stegosaurus)和「三角龍」(Triceratops)。我小時候經常往費城的富蘭克林科技館(Frank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跑,去看那裡所有的骨頭化石,然後就愛上恐龍了。
斯皮爾伯格:我就知道你會提這壺!這是不是很糟糕?我三番五次走溫情路線。要不是之前有過「9·11」事件,我是不可能完成《世界之戰》的。因為《世界之戰》就以「9·11」事件為原型,那是在美國歷史和全球恐怖主義歷史上的一件大事。美國不是一個習慣於受到襲擊的國家,上次我們被襲擊還得追溯到珍珠港事件。
斯皮爾伯格:在我小的時候,我常常會把冰棒棍收集起來,然後我會基本上只靠膠水把它們粘成一隻恐龍的樣子。我會在後
read.99csw.com院里挖一個坑,然後把它埋在裏面,接下來我會等上一周,然後我會再去挖掘它。那是我離成為一個業餘古生物學家最近的一次了。斯坦利要是看到了那種場景,他或許會瘋掉的,在他看這部電影時,銀幕上是不會缺少那種真實的亮黑的,因為他周圍可沒那麼多的大麻煙霧。我在觀影條件比較好的環境下又把它看了七八遍。但那個周末首映……我甚至認為他們回過頭把營銷策略都改了,稱它是「銷魂之旅」,因為它招惹來了——毒品文化。
斯皮爾伯格:一種完全不同的場景,沒錯。
卡梅隆:據我所知,他從未和任何其他電影人有過這樣的關係。

在斯皮爾伯格的電影《侏羅紀公園》中,古生物學家艾倫·格蘭特與霸王龍來了個面對面。
Jurassic Park © Universal Pictures.Image courtesy of Photofest.
斯皮爾伯格:如果你願意,《世界之戰》是能當成一本精神典籍來讀的,這也許就是科幻的偉大之處。
對我而言,《2001:太空漫遊》給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深遠的影響。那時我還在上大學,那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讓我產生出了一種宗教體驗感的觀影經歷,而我當時並不是喝醉了。我一不抽煙二不嗑藥,滴酒不沾,我是一個挺潔身自好的人。周末首映時我去電影院第一次觀看《2001:太空漫遊》,兩件事讓我記憶猶新:第一,太空的景象並不像我之前所想象的那樣濃黑;第二,畫面的對比度不夠。但你知道為什麼畫面的對比度不夠嗎?因為影院的每個人都在抽大麻,他們真是把空氣和氛圍都給毀了。
卡梅隆:因此,我們是在把我們自己投射到機器上,然後又將機器人格化了。不過目前有一種光明正大的努力正在進行,在大量資金的支持下,它正勢不可當地向著創造人工意識的方向進軍,這種人工意識要與我們自己的意識一樣,也不排除遠遠比人類意識更高級的可能。我們此刻正生活在一個科幻世界里。我想說,《2001:太空漫遊》中的電腦哈爾(HAL)可能將會在我們有生之年中出現。
卡梅隆:所以,要說哪個人是在用他畢生的創作生涯來驅除童年時代的惡魔,你就是一個經典例子。

1936年影片《篤定發生》(Things to Come)的電影海報,原著作者是科幻界的傳奇人物H.G.威爾斯。
H. G. Wells'Things to Come © United Artists.
卡梅隆:這麼說,你從來沒被《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里的那些飛猴子嚇過嘍?
斯皮爾伯格:我們去過他家裡,還看了他的那些了不起的收藏。
卡梅隆:好吧。關於它我的感受稍有不同。我讓人給我寄了這本書,因為我聽說它即將發售。書是周五晚上收到的,當天晚上我沒有看它,周六才開始讀這本書。當我讀到霸王龍舔汽車擋風玻璃,而孩子們還在車裡面的那一幕時——在電影中你實際上沒讓它舔玻璃,但書里是這樣寫的。我就說,「我一定要把這個拍成電影」。說這話時,我連書都還沒看完呢。我立馬打電話過去,但對方回復說,「史蒂文剛把它買下了」。在可能發生的事情裏面,這得說是最好的一個了,因為如果讓我來拍的話,我會把它拍成《異形》那樣的,我會把它拍成一部嚇得人屁滾尿流的限制級電影。你把它拍得也夠嚇人了,但仍適合給孩子們看,你是對著12歲的自己來拍它的。
斯皮爾伯格:在《第三類接觸》里,沒錯。在你還很小的時候,所有這些東西會銘刻在你的腦子裡,你自己也不想把它們給扔掉。我認為作為一個電影創作者,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這種童心,最起碼在講那類能把我們吸引住的、令人驚嘆和敬畏的故事時應該是這樣。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當我們在領會每一樣東西時,我們得不斷與天性里的那種憤世嫉俗的衝動做鬥爭。那就是一場戰鬥。

斯坦利·庫布里克執導的《2001:太空漫遊》的電影海報,這幅海報利用上了它「電影迷|幻|葯」的名聲。
2001: A Space Odyssey © MGM. Image courtesy of Photofest.
卡梅隆:你是不是花了很多時間來盯著天空?
卡梅隆:有段時期樣樣東西都帶著尾鰭。
卡梅隆:他有最頂級的收藏品。
卡梅隆:那一幕出現在了影片《第三類接觸》中,同樣的場景。
斯皮爾伯格:我在電影院里看到有個傢伙,他展開雙臂走向了銀幕,然後竟然從銀幕中間穿過去了。後來才有人告訴我們,那銀幕是一條一條的。它實際上並不是一整塊白布。
斯皮爾伯格:我原來沒想過要把《E.T.》拍成一個講外星人的電影,它原本是一個要講我的父親和母親離婚的故事。我最初寫的故事——本來不是一個劇本——所講的內容大致就是你的父母分開了,然後他們分別搬到了不同的州去住。在創作《第三類接觸》之前我就一直在寫這個故事。當我在拍《第三類接觸》中那個矮小的外星人普克(Puck),走出了母船並做著柯達伊手勢(Kodaly hand signs)的場景時,各種思路匯到了一起。我想,等一下!假如那個外星人沒有轉身回到飛船里去會怎樣?假如他留下來了呢?或者假使他甚至迷了路,然後孤立無援地被困在這裏了又會怎樣?如果一個父母離異了的孩子,或者這個離了婚的家庭有一個需要填補的巨大空洞,而這孩子又拿他新認識的外星好朋友來填補這個空洞的話,又會發生什麼事?《E.T.》的整個故事就這樣與《第三類接觸》的場景走到了一起。
卡梅隆:在影片《人工智慧》中,你實際上表現了未來人類在向著機器人或機器基質的一種轉變——甚至都不是真正的人類,只是這個星球上的我們的繼承者。
斯皮爾伯格:為什麼我們要同Siri交談?我們幾乎把任何東西都給人格化了。一般從孩童期開始——如果你是個小女孩,你就會有一些洋娃娃,如果你是個小男孩,你就會有好多小變形金剛和塑料大兵玩具。我總說每個小孩開始時都是講故事能手,因為他們的想象力豐富得無邊無際,而這種想象力能幫我們決定一種鏡頭角度。作為小孩子,我們會趴在地板上,讓我們的視線儘可能與地面平齊,這樣那些小玩具人就會看起來超真實。如果我們有電動火車,我們就把視線與鐵軌平齊,然後讓火車一圈一圈地跑。
斯皮爾伯格:但我要只給他配上這張臉,只有做母親的才會喜歡。我不想讓E.T.變成一個可愛的傢伙,想讓它有點笨拙,長著一個礙手礙腳的大肚子,有個若像人一樣穿上衣服就會顯得過細的脖子。當這樣一個腦袋頂在一根像潛望鏡一樣的脖子上,我想讓人們說,「老天,這太真實了!這絕不是一個穿戲服的演員扮的!」——雖然在某些行進鏡頭中,我們的確找了些穿戲服的演員去扮他。讓E.T.的外觀既能贏得觀眾的喜愛又能贏得觀眾的尊敬,這非常重要。我不想讓一個可愛小巧的迪士尼人物從那扇大門裡走出來,讓滿場觀眾異口同聲地發出一聲「喔」!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事情。編劇梅利莎·馬西森(Melissa Mathison)與我想法完全一致。她寫了一個出色的劇本,而且梅利莎不斷在強調,「E.T.必須是一個孩子,必須擁有孩子一樣的特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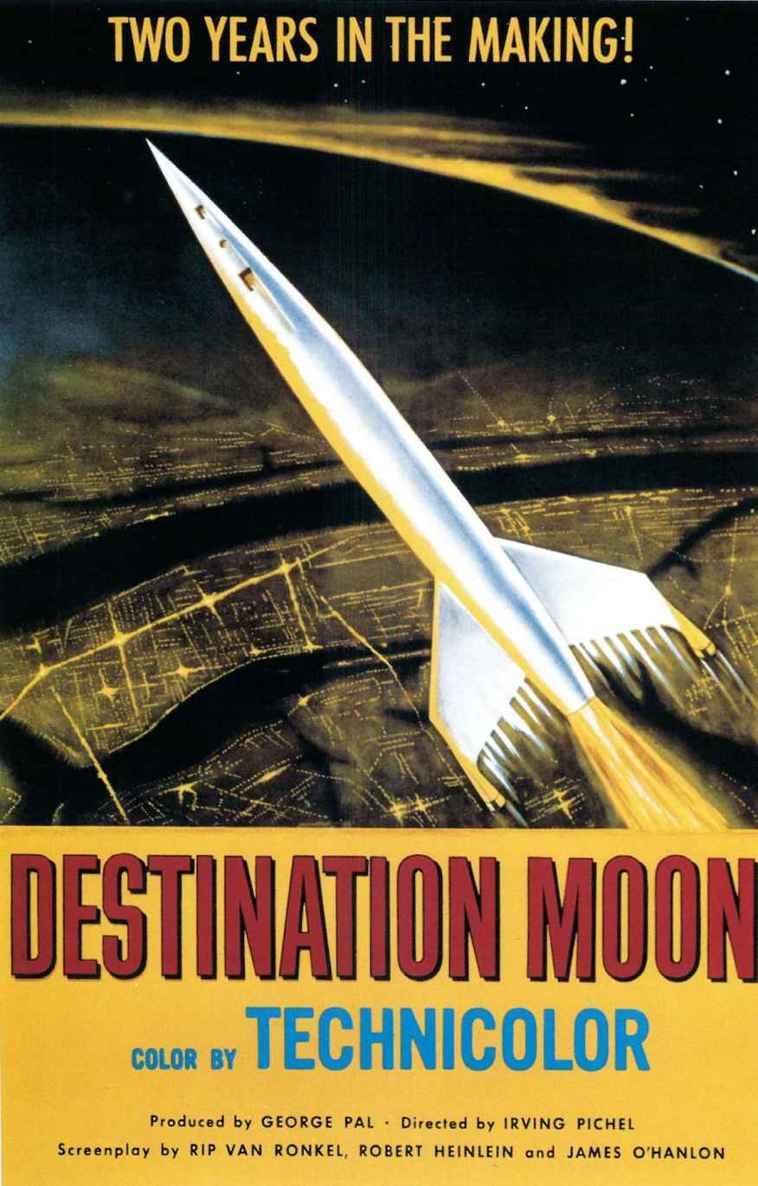
1950年的經典科幻電影《登陸月球》的電影海報。
Destination Moon © Eagle Lion Films Inc.
卡梅隆:還有如果你輕信了黑心老太太,她就會把你放進爐子里烤著吃了。要聽父母的話,都是些警世的寓言故事。但在我看來,當我們進入了科技時代,這些警世寓言恰恰可以用來應對我們的恐懼和焦慮——我們對這一切正在往何處去這個巨大的人類實驗的焦慮。
卡梅隆:那正是製作《阿麗塔:戰鬥天使》(Alita:Battle Angel,改編自同名人氣漫畫的電影,將由羅伯特·羅德里格斯〔Robert Rodriguez〕執導)使我感到興奮的地方。不是為了塞點我自己的東西,而是對這樣一種想法——如果你打算創作出人類的幻影那樣的某個角色,用CG動畫來實現它。我寫這部電影的劇本時,那還是在10年前,我想著它永遠都達不到十分完美,但我認為現在我們能把它製作得最接近於完美。如今,這幾乎是一個自掘墳墓式的觀念,因為那時仍然存在「恐怖谷」(uncanny valley),當看到一個極其接近人類但某個地方還是有點走樣的機器人或模擬人,人們會產生強烈的負面反應。
斯皮爾伯格:正是如此,我喜歡我們撥號打電話的那些日子。我不知道我是否懷念撥號電話,但我懷念人們真的還記得它的這個事實。我的孩子們或許會看著它,但不理解這物件是個什麼東西。它要讓你費點事才能與某個人交流。你必須坐到一台打字機前面,用手一個字母一個字母打出詞句。你必須手寫一封信,或者你必須真的撥出一串號碼。要想做到與某個人通話和交流,就得費點工夫。而通信在今天幾乎就是習以為常,不費吹灰之力。要不了多久,我們還會實現能繞開任何實體技術和平台技術的更先進的生物技術,那些舊的技術就沒用了,每樣東西都直接能與我們的大腦皮層進行連接。這都是近在眼前的事。
斯皮爾伯格:是的,一模一樣,我把這個場景放進了《第三類接觸》中。我倆靠著他的軍用背包躺了下來,然後我們抬頭看著天空。大概每過半分鐘左右,就有一道燦爛的閃光劃過夜空。有好幾次,其中的幾顆流星還爆成了三四片。